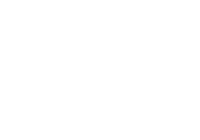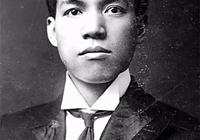最成功的“知識經濟”商人羅振宇,剛剛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知識發佈會”,深圳衛視和優酷同步直播。羅振宇說,他的知識付費app,在過去的一年獲得了超過1000萬用戶。

比這場發佈會早幾天,著名知識分子、作家許知遠的訪談節目《十三邀》第二季上線了。首場嘉賓是著名的文化人、現象級綜藝節目《奇葩說》的製作人馬東。在訪談中許知遠問馬東:你喜歡這個時代麼?馬東說:喜歡。許知遠問他:你說這話的時候沒有半點猶豫麼?馬東臉上微微露出了一點複雜的表情,說:沒有。許知遠有點尷尬地向後仰了一下,笑著說:那我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很多人覺得,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許知遠問了太多不合時宜的問題,最終讓他自己陷入尷尬,他有著太多的偏見預設和“嚴肅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而馬東那句“我沒那麼自戀”簡直就是抽向許知遠的一記漂亮的耳光。許知遠根本就沒有與他人對話的能力,因為他從來不嘗試著理解別人,他的思維結構僵化到不能容納任何新的東西,為什麼讀博爾赫斯才是知識分子,而錄製《奇葩說》就不是知識分子的本分呢?為什麼馬東在澳洲留過學,就一定要在你讀關於悉尼的文字的時候流露出悵惘回眸的神態呢?馬東說他喜歡這個時代你就很費解,你有什麼可費解的呢?
把許知遠跟馬東的“尬聊”理解成一個迂闊不思變通的老派知識分子和一個聰明狡黠的文化生意人之間的雞同鴨講,是一個很有戲劇張力的場景。但其實我覺得,許知遠說的,馬東都懂,馬東的意思,許知遠也懂。吧馬東那句“你的本色是憤怒,我的本色是悲涼”highlight 出來放在標題裡的,是許知遠的“單向空間”團隊,不是其他人。
憤怒何態、悲涼何故,在看似話不投機的交鋒中,兩個人都get到了。
這是《十三邀》的第二季開場對話,第一季的開場嘉賓,不是別人,就是羅振宇。許知遠和羅振宇之間,也有類似的交鋒:許知遠也把他對這個世界的迷惘、質疑和憤怒全盤拋給了羅振宇,羅振宇也是逐一拆招。作為追求黃鐘大呂般經典閱讀的知識分子,許知遠肯定不全然理解羅振宇批發的散裝零售知識有什麼意義,他說:我就是個唱輓歌的人,你不覺得輓歌很美麼?羅振宇說:唱輓歌是在浪費生命。
羅振宇未嘗不理解輓歌的頓挫之美,但他不唱,或者不在公開場合大聲地唱出來。許知遠也不會據此認為羅振宇是一個顢頇無知之輩,雖然略矜持迂闊,但他畢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許知遠、馬東和羅振宇,他們三個人其實是一路人,他們是中年人,也是知識分子。
許知遠生於1976年,馬東生於1968年,羅振宇生於1973年,都過了不惑之年。讓這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四十而不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為這代人從出生到成長,再到過完半輩子的過程,整個中國社會都在經歷著大悲大喜的跌宕,伴之以不期而遇的興奮、衝動和困惑。比起上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知識結構更完整,見過和經歷的更多元,感知世界觀和價值觀衝擊也更豐富:東方與西方、技術與人文、經濟與倫理、社會座標上的左與右……從文化底色上,他們是接近的。
而且他們都在人生的上半場抓住了機會,無論是時代的還是個人的。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許知遠,社會文化節目主持人的馬東和財經商業節目主持人的羅振宇,都找到了在這個社會上屬於他們的人物設定,而且都做得很不錯。
但不期而遇的宿命是:在2010年之後,他們都進入了中年,他們的各自的人物設定都被挑戰了,中年危機也開始了。
移動互聯網來了,人工智能接著還要來,媒介越來越碎片化,娛樂至死從理論變成了現實,二次元入侵三次元,傳統和經典的宏大敘事——無論是商業的、社會的還是人文的,都在快速瓦解坍塌,社會更撕裂和多元,人性更脆弱,自由表達越來越變得不可能……有的人的中年危機就是一個保溫杯,可對這些有知識、有資源、有名望和有表達能力的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的中年危機。
人們不讀博爾赫斯了,不看電視了,不看紙質書甚至連電子書也看不下去了,不相信理想主義了,不討論形而上學了,年輕人不愛聽大道理了,不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了,“喪”比“正能量”可愛了。這麼下去,他們的書誰買,他們的節目誰看,他們的社會價值在哪兒?
重要的是,當人生上半場的很多自我設計和建構局部崩塌之後,他們還理解不理解這個世界,他們又該如何自處?
仨人都頓挫過。馬東2013年從央視離職之後打了8個月的高爾夫,標準的中年危機生活;結束了在央視財經頻道和第一財經當主持人的日子,羅振宇一度有近兩年不知道該幹些什麼;而許知遠,在很多書不能出,很多文章沒法發表,很多年輕人不再把他當成知識偶像之後,一直在質疑,在憤怒。
也幾乎是在同時,三個人找到了各自的解藥。
2012年底,羅振宇開始了《羅輯思維》;2013年底,許知遠和他的團隊拿了一筆投資,“單向街書店”升級為單向空間新媒體;2014年底,馬東在愛奇藝製作的說話達人綜藝節目《奇葩說》上線。
羅振宇開始了散裝零售知識批發的生涯,從每週一期視頻,每天一段音頻,到現在的散裝知識付費商店“得到”。羅振宇消解了知識,把成章節的、系統的、卷帙浩繁的商業和文化知識體系掰開了揉碎了,變成一個個故事、一個個段子,一段段談資、一條條祕籍和一件件工具,餵給那些需要用知識填充碎片時間和空虛大腦的人們,他不指望人們從樹木中望穿森林,只在乎這些散落的知識容易被獲取、直接能拿來用。
它變成了一個估值幾十億人民幣的生意。羅振宇甚至越來越往幕後縮,不再出來佈道,不再販賣他的知識和價值觀。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生意人,不是什麼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他愛這個能讓他賺到錢的時代,他不需要唱輓歌。在“知識發佈會”上,他跟信眾們說:書是讀不完的,都來買零售的知識吧。
作為知識生意人的羅振宇成功了,這比做財經頻道主持人更讓他有成就感。倡導散裝零售知識的他還讀書麼?當許知遠疑惑地問他“這個時代不需要輓歌麼”的時候,他真正在想什麼?他可能說了一些,但更多的,他應該沒說,但他心裡清楚。這幾年,很多中國企業家的命運大起大落,在歷史的註腳面前宛若塵埃,熟悉他們過往曾經的羅振宇看著這一切,內心裡吟唱過輓歌麼?

馬東炮製了《奇葩說》這麼一檔現象級綜藝節目,而且成功了。一檔有智識和思辨含量的節目能獲得人氣和商業上的雙重成功,靠的真不只是運氣。這檔節目裡有素人,有明星,有兩岸三地的知識分子,有犀利善辯的妖孽鮮肉,當然還有羅振宇,甚至雷軍和李開復。他們辯論的都是年輕人關心和困惑的話題,從接受不接受開放式婚姻,到整容重要不重要;從長生不老是不是好事,到要不要幫失憶的戀人一鍵恢復記憶。有的現實,有的飄渺;有的形而下,有的很形而上;有的關於社會和倫理,有的觸摸了人文和終極哲學。要談得有趣、有料,還得有八卦、有鮮明人設和娛樂性——作為出品人,馬東改變了很多。
他擅長讓這事變得有內涵和有料,但也和他的搭檔蔡康永、明星辯手顏如晶和姜思達等人那樣,穿上了很誇張的戲裝,把頭髮挑染成了不太常見的顏色。那些90後辯手覺得馬東“挺俗的一人,跟我們挺聊得來的”,這應該是馬東追求和想要的,但這個未必是100%真實的馬東。他用這種方式製造了一款現象級的綜藝節目,一個很賺錢也值錢的文創生意,也用這種方式讓自己試圖變得更年輕。
年輕是一件好事,可以用來對抗衰老憂心忡忡,這就是王朔說的“人老的標誌不是守舊,而是維新”。“熱愛這個時代”的馬東對這個時代的真正看法是什麼?我跟《奇葩說》的個別辯手有一點私交,很多辯手私下裡是很嚴肅和厚重的人,關心一些很深沉和焦灼的時代敘事和話題。顯然,這些話題不可能拿到《奇葩說》的節目上來,但作為“過來人”的馬東,私下裡會跟他們聊這些話題麼?當馬東說出“我的本色是悲涼”的時候,那個把一個臃腫而滄桑的身軀包在五顏六色的衣服裡的馬東,從我的眼前倏地消失了,那個瞬間,他的魚尾紋裡真的寫滿了悲涼。

而許知遠,是被誤解最多的那一個。
看上去,他仍然泥古不化,他出差的時候仍然在高鐵上蜷著腳,一邊摸著自己的大腿一邊讀很厚的紙質書,在上面圈圈點點;他仍然希望寫一部史上最好的《梁啟超傳》;他仍然用自己的信仰和堅守,對抗著時代的車輪。但除了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身份,許知遠現在的另一個身份是“單向空間”創始人,經營微信公眾號、音頻、視頻訪談節目、“單向歷”這樣的文創周邊產品,當然還有書店。
他的一些知識,也被零售了。
其實,許知遠很入世,但方式不同。比起羅振宇和馬東,他少了迂迴和閃避,多了單刀直入。羅振宇和馬東把自己的本質拆碎了,揉在了節目裡和散裝的知識裡,藏得很好;許知遠把他的鏡頭感、音頻的節奏駕馭等一些新媒體運營的技巧遮蔽在了他對大時代的焦慮和憤怒裡,藏得也不錯。許知遠“入世”的方式,就是去跟那些和他“道不同”的人聊天,把他的焦灼、困惑、不安和異議直愣愣地拋給對方,他知道對方會反駁,會否認,甚至反脣相譏;但他不在乎,他也不會在最後的節目裡剪去這些尷尬的場景,因為這些尷尬本身,就是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的尷尬,他從來沒打算迴避它們。
他不是一個不能容納任何新想法和新事物的人,他也是一個不錯的新媒體經營者。他在鏡頭前面毫不避諱地流露出他對俞飛鴻的喜愛甚至花痴;他在跟一群二次元coser對話的時候一臉困惑,他不喜歡二次元,也在用自己的認知框架去“冒犯”她們,但他真的在聽她們說什麼,而且最後好像也被說服了。這些過程,這些鏡頭,都很真實,但也很有戲劇張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許知遠還是那個焦慮憤怒的知識分子許知遠,但他在鏡頭面前“演”得還真不錯。
對一個對世界有認知、對自己有判斷同時又絮絮叨叨的中年人來說,化解“中年危機”的另一種方式,其實就是把自己的焦灼和危機感暴露於大庭廣眾,本色地與世界上那些他不理解、不適應和無能為力的事物直接對抗和交鋒,在這個“互相傷害”的過程完成與世界的和解,與自己的和解。在很多時候,《十三邀》給我們呈現的就是這麼一種感覺。
而且作為一檔那麼嚴肅的談話節目,《十三邀》已經算是成功了。

從社會影響力上,它不能跟《羅輯思維》和《奇葩說》相比,但思想的交鋒從來就不是以粉絲多少、估值高低和財富多寡為前提的。羅振宇和馬東為什麼上許知遠的《十三邀》?單純地為了推廣和營銷麼?許知遠的聽眾有多少會是《羅輯思維》、“得到”和《奇葩說》的粉絲?那些聽羅輯思維的人、在“得到”上買名人格言的人和為了支持馬薇薇或肖驍爭得勢不兩立的人,又能有幾個人知道許知遠是誰?他們之所以願意花幾個小時的時間跟許知遠坐下來,除了市場和公關的需求,恐怕更重要的是:他們面對面地坐下,互相凝視著對方,幾個小時的時間,他們的交流是充分和盡興的。
這種交流在這個時代已經很奢侈了。
許知遠把一些尷尬的問題扔給羅振宇和馬東的時候,他們知道他的意思。他們在鏡頭前面,用一些有技巧的方式否認和回擊的時候,背後的潛臺詞,互相應該都懂。“和而不同”是一個很套路的說法,他們在節目裡需要呈現這個,但背後那些“和而同”的暗號,他們互相應該能接得住。
畢竟這些讀過書、經歷過事、見證過時代際遇變化的老男人都知道,中年是一段漫長而難捱的時光。這麼幾個小時的交鋒,對誰都沒有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