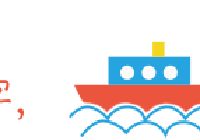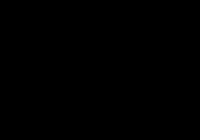冬天的記憶:酸菜
文|阿棉
圖|源自網絡
下了幾場雨,初冬的跡象愈發明顯了,乾冷的空氣在城市裡竄來竄去,風呼呼的在夜半的窗外響起,聽來屋頂都似有被掀翻的可能。
若是在舊年的冬日裡,早已開始慌慌的囤菜了。街角常有小皮卡停駐著,一車的大白菜,或土豆或蔥。成筐的被周圍的住戶買了,作為過冬必備的蔬菜。有了這些菜,心裡是有底的,再酷冷的寒冬也是不怕的。
大白菜一半留著,可以炒菜、包餃子,另一半用來醃酸菜。北方人家家戶戶都有著醃酸菜的習慣,院子裡最醒目的就是一口醃菜大缸了,被主人擦的鋥亮。
也曾看過姥爺醃菜,先把大白菜洗淨瀝了水分,一層層碼在缸裡,撒上粗鹽粒,再倒入熬了花椒的水,最上層壓了青石,過了一個月就可以食用,一缸的酸菜可以吃一個冬天。
醃菜看似簡單,每個人醃製出的味道卻是大相徑庭,有的是酸脆,有的則齁鹹,老輩人說這跟手氣有關。
我很少看到姥姥醃酸菜,據說她小時抓過麻雀,壞了手氣。也曾吃過一次,醃菜的味道真不敢恭維。
寒冬裡最考量的便是撈酸菜了。下一場雪,酸菜汁更冰冷了,手伸進去時,寒氣直侵入骨髓。只是一想到酸菜羊肉,便是什麼也不怕了。
酸菜羊肉在我看來,可謂是絕配。醃製過的白菜失了鮮活,多了酸鹹之味,有些涼性。而羊肉是熱性的,它的膩裹了酸菜的寡淡,也中和了酸菜的涼,再撒上辣椒麵,那味道是整個冬季裡最絕美的。
棉式酸菜
酸菜在缸裡日益減少著,需得伸了半個胳膊才能撈到,姥姥卻是捨不得倒掉那大半的酸菜汁,如寶貝一樣的儲存著,儘管那酸汁裡起了白色的沫。姥姥說,這是解煤煙味的良藥,我是不大信的。
姥爺是親戚裡最早住樓房的。八十年代的樓房裡沒有暖氣,家家都得架爐子。夏天還好說,到了冬天取暖就得在屋中央支個鐵爐,煙囪通過牆洞鑽出去,火生的旺,姥姥常會烤些紅薯和土豆。
封爐子也是個技術活,煤餅壓的太少,爐火在半夜不聲不響的熄滅了。煤餅太多,整個屋子裡都會充斥著煤煙味,一早醒來昏昏沉沉的,一看症狀,就知道是被煤煙打了。
我也被打過一次,暈乎乎的還有點噁心。姥姥二話不說,就去酸菜缸裡舀了碗酸菜汁,硬逼著我灌了進去。酸涼的汁水驅散了反胃,又呼吸了新鮮的空氣,人清爽了不少。不僅對姥姥的智慧佩服有加,對那口酸菜缸也更加愛護了。
曾經蒼白的日子,如今被歲月修飾的色彩斑斕。那些最看重的,漸漸失去了地位。已經很久沒有囤菜了,酸菜也從日常的菜譜裡退了下來,家裡的醃菜缸早已失了蹤跡。市場上看到叫賣的酸菜,也只是餐桌上偶爾的點綴。
我卻還是喜歡酸菜的味道。它是那些年貧困日子裡最好的支撐,無法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