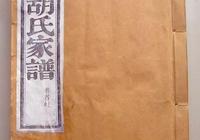《邢臺老沙河城胡氏家族補遺》之四
邢臺老沙河城的胡氏墓園
作者:胡順安

邢臺老沙河城胡氏墓園的主體,1970年代以前,位於沙河縣城北關的閣樓之北,古御路之東,緊鄰官道。當地人俗稱“胡家墳”。
邢臺老沙河城的胡氏家族自明初奉詔從山西遷來,初居縣西的綦村。因先人科考入仕,徙至縣城。明朝萬曆年間,沙河城籍人士胡三顧鄉試中舉,出任新泰縣令。勤政愛民,政聲卓著,備受群眾愛戴和皇帝讚賞。胡三顧辭世後,皇帝為表彰他,在其籍貫沙河城北的御路旁邊選址敕建墓園和牌坊,並賜神道碑(縣誌有載),記載其生平功績。
由此,沙河城胡氏後人去世後陸續殯葬斯地。自明朝迄1970年代,歷經明清、民國,延續至今,前後凡數百年,墳塋增多,墓園日益擴大。
上世紀八十年初,附近幾位八十多歲以上的文化老人回憶描述道,七十多年前,他們記事的時候,胡家墳坐東朝西,南北長近二百米,東西寬約百米,佔地近百畝。墓園大門坐落在西南方位,是一座由巨大的長方青石條構築的四柱牌坊,寬約六米,高五米左右。橫樑上書寫著端莊大氣的隸體大字“沙河城胡氏墓園”。立柱上陰刻著“祥光燦爛照先祖 瑞氣蒸騰裕後昆”,字的下面畫有兩種圖案,上為牡丹,下是蓮花,牡丹象徵富貴,這兩種圖案意為“連連富貴”。石門兩側分置兩個蹲坐的大石獅。門旁建有一個三米多高的旗杆,上邊有浮雕紋飾等,旁置上馬石。氣勢雄偉,莊嚴肅穆。可惜,這些大約在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被毀壞了。
走進墓園,左拐,緩緩步入甬道。內中的主體構建設施均為坐北面南朝向。甬道兩側,分別排列著石獸,有獅子(象徵威武)、虎(象徵威嚴)、麒麟(象徵吉祥太平)、馬(象徵仁義)、羊(象徵忠孝)等。曾記得,高大的石馬頸部浮雕著斜向的韁繩。此外,還有若干尊比真人略高的石人,俱是文官武將。文官,髮簪高束,臉龐寬大,慈眉善目,嘴巴微抿,鬍鬚飄逸,表情莊重,或手執書卷,或持古樂器,或作揖禮狀;武將,穿著盔甲,全身將軍裝束。天庭飽滿,眼睛突出,上脣留有兩撤八字鬍鬚,右手按著一把掛在腰際的長劍或其他古代兵器。表情嚴肅, 怒目威視,彷彿威武的將士在巡視領土和保護主人。
墓園深處,若干凸出的小丘臺前,聳立著很多三四米高、寬厚不一的石碑,櫛比相鄰,錯落有致。部分巨型的龜座青石碑或個別漢白玉碑的正面上端橫向書寫“光前裕後”、“流芳百世”,及墓主的大名等,背面陰刻著墓主的簡介。石碑之上端,或鏤空,或浮雕著多種花飾、神獸等。部分具有高貴身份的先祖石碑旁,還建有三四米寬、四五米高的石質牌坊,按照忠孝節義排序。橫樑上斗拱飛簷,中間橫匾陽刻著莊重的御題或當地要員的大字“恩光十世”、 “功德顯赫”、 “皇恩寵賜”、 “樂善好施”、“立節完孤”等,有的豎額上也題有辭聯。
園內所有石器的雕技,採用浮雕、圓雕、透雕和陽刻、陰刻等多種手法,線條鮮明有力,流暢逼真;塑像雖形狀各異,皆端莊細膩,造型美觀,眉目傳神,栩栩如生。
民國初期,“胡氏墓園”前仍有花壇,園內樹木繁多,松柏鬱蔥,綠林成蔭,聞名鄉里。若在夏季,行人路過,常於墓園小憩納涼。
當地的老人們傳說,“胡氏墓園”在民國之前享受“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禮遇,非常榮耀。
清末民初,社會動盪不安。胡姓主脈的遷墳,始自光緒年間進士、吏部註冊知縣胡人元去世後,其子嗣將其和上一代先祖的墳塋一併遷葬於去舊址東北約四里許的祖田,敕建旗杆和牌坊(即當地人平時所說“棋杆墩兒”的地方。參見拙文《邢臺老沙河城“旗杆墩兒”的來歷》)。1920年代之後,由於戰亂不斷、社會變革加劇等諸多因素,沙河城胡姓主脈的近親後嗣也陸續隨葬到這裡。不久,胡姓家族另一支脈的子嗣購得並遷葬到北行距離祖墳約一二里地的地方,在十里鋪路和張莊路之間,東西綿延與附近的馬家墳和尤氏墳地相連,人們稱之胡馬墳或胡馬尤墳。
一九三零至一九五零年代初期,時局興替,胡姓主脈的大部分族人和支脈的個別人家遭受嚴重的不公正對待,生活難以為繼。族長決定將胡氏新舊墓園成材的樹木全部砍伐賣掉,以救濟陷入生活困難的族人。
到1958年之後,墓園的北段,東端,分別劃給北街第六、七、八等生產隊當耕地;南部劃給北街第六生產隊做打晒糧食的場所。墓園南部的少量餘地則無人使用和管理,曾一度雜草叢生,許多石人石獸和牌坊石碑等不斷慘遭毀壞,淒涼至極。
1960-1970年代末期,墓園內仍遺有部分殘損的石人、石羊、石馬、石虎,還有無頭的龜座、半截的石碑,以及歪斜的牌坊青石條等。我記事的時候,常相約結伴去“胡氏墓園”玩耍。特別在夏秋季節,我們揹著挎簍去“胡氏墓園”或附近割豬草,交與生產隊做豬牛的飼料,以換得工分。我們喜歡去那裡,並非因為那裡地肥草美,而是那裡有牌坊和很多石碑、石人和石羊石馬等,還有很多的大樹坑,坑的四周滋生著小樹。這些都可供我們玩耍。我們正處調皮的年齡段,當年的文化生活單調枯燥,又無多少可供少兒享用的其它遊玩場所或玩具。附近村莊的很多孩子也常三人一夥、五人一群地聚結於此。
我們穿行於殘損的石碑、石羊石馬和傾圮的牌坊之間,盡情玩耍。或分組捉迷藏,躲藏遊跑於小樹叢和石碑石馬附近;或比賽攀爬,相互踩著肩膀,拉拽著攀爬石羊石馬和小樹等。個別完整些的牌坊和石碑太高,我們一般不敢攀爬,也上不去。有時候,即使我們偶爾互相踩肩和搭拽著,或藉助附近的樹木爬上去了,在孤高的青石上,也不容易下來,很危險,驚慌害怕得哭喊著,讓旁邊的其他大朋友或路過的成年人幫助下來。所以我們一般不攀爬這些孤立高直的石器構件。
我們常常玩得忘乎所以,待突然發現臨近中午或黃昏,才匆匆割些豬草回去交差。
1970年代,我們曾經被學校組織去“胡氏墓園”平墳。我們一群學生拿著鐵鍬和钁頭等,雄赳赳的奔赴那裡。挖去浮土,掘開一層用厚大藍磚壘砌的穹頂外槨,小心翼翼的下去,捂著鼻子,打著手電,搜尋到一些冥具,拿著玩兒。記得有的石碑或石條被拉到沙河中學墊做“萬人批判大會”會臺的基礎,更多的則被附近村民拉走墊做房基。由於當年的政治環境,胡氏後嗣沒人敢對此有任何表示,只能默默看著祖墳被挖。那時候,我們年幼無知,少不更事。極少數殘碑散遺在北關閣樓的附近,多年後被文物販子販賣或盜走。
至此,短短數十年間,老沙河城曾經榮耀數百年的宏大“胡氏墓園”徹底衰敗消失。老沙河城的文化遭到嚴重破壞,是整個社會的隱痛,也給沙河城的人文歷史留下一道疤痕和深深的遺憾。
現在偶爾回憶起來,仍感驚歎,在那個當地青石缺乏,運輸和技術落後的時代,先祖們是如何將那麼龐大完整的青石條運來和安裝起來的。然而,在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中,此地的舊景早已時過境遷,蕩然無存,只能留在當地現在五十歲以上人們的隱約記憶和坊間傳說中了。
初稿於2011-04-18,修定於201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