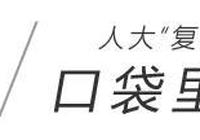▎文末有活動
學界圍繞新文化運動的探討與反思從未停止。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影響最大的反思聲音主要有兩種:一,對“激進”與“革命”的批判,認為“夭折的憲政”當歸咎於“倒退的五四”;二,“救亡壓倒啟蒙”,激進民族主義導致近代轉型功虧一簣。
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紀》,刊髮長文《重論“大五四”的主調,及其何以被“壓倒”——新文化運動百年祭》。秦暉認為,這兩種說法只看到了一些現象,但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並非“救亡壓倒啟蒙”,儒家思想是啟蒙的內在動力。(本次推送,摘編該文主要觀點)
李澤厚錯了:
新文化運動並非“救亡壓倒啟蒙”
對於1980年代以來由李澤厚暢言的“救亡壓倒啟蒙”之說,到1990年代又宣傳“告別革命”論且不放棄前說,秦暉認為李澤厚陷入了巨大的矛盾,“這就像一個法國人既惋惜盧梭學說之被‘壓倒’,又痛罵大革命之鴟張”。並且,當時宣稱的所謂被“壓倒”的“啟蒙”,並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那恰恰是從五四起成為大潮的),如果“救亡”指的是民族主義,那應該說從晚清起,“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啟蒙”的內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內容之一。所以,“說穿了,‘救亡壓倒啟蒙’實際上指的是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並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崛起”。
但是,“壓倒啟蒙”的是“救亡”嗎?秦暉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使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並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崛起的說法在歷史解釋中站不住腳:
首先,民族主義如果與自由主義衝突,它怎麼又會與列寧主義結合?眾所周知,儘管列寧主義在後來的歲月裡的確演變成了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運動引進它之時,卻是以極度排斥民族主義而著稱的。在1917年的列寧那裡,“愛國主義”、“護國主義”,甚至“革命護國主義”都是“反動派”的代名詞。在一戰時期的歐洲和俄國,一般左派反戰運動只是主張和平,烈寧卻主張“變外戰為內戰”、“使本國政府戰敗”,在很多俄國人看來,沒有比這種主張更“賣國”的了。雖然掌權後的列寧又一轉而變為極端地擴張蘇俄勢力,但也不是在“愛國”或“民族主義”的七號下,而是繼承馬克思“工人沒有祖國”的傳統,在“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的旗號下實行此一轉變的。
同樣,儘管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幾十年後也日益變成了“中國崛起”、“中國夢”式的民族主義,但是當初它在中國激起的與其說是民族主義,不如說是打著“國際主義”旗號的親蘇情緒。當時的親蘇者尤其是其中堅,主要並不是把蘇聯視為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合縱連橫的助力,而是把蘇聯的制度視為比自由主義更“進步”的人類理想,因此而親蘇信蘇的。這不就難理解在後來的三十年裡,當中蘇主權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總是向蘇聯“一面倒”,甚至在1929年蘇聯軍隊大舉入侵中國的“中東路事件”中,還打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
另外,我們習慣於強調一戰後巴黎和會刺激了民族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佔據上風,並且,金觀濤和劉青峰運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分析以數值證明:
在新文化運動主要陣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時期提到的國內外大事中,一戰(歐戰、世界大戰、歐洲戰爭)遙佔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紙杯提及287次;國內事件被提及的兩次帝制企圖(張勳復辟和洪憲帝制)只有113次,其他如義和團、辛亥革命等,提及次數就更少了。
巴黎和會
同時,數據庫還顯示:“巴黎和會在1919年‘小五四’時期雖為社會熱點,但以思想文化評論而非新聞報道定為的《新青年》其實沒怎麼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後,即陳獨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轉向馬克思主義後,才大量提及巴黎和會。”金觀濤、劉青峰據此分析:“巴黎和會雖是五四當天遊行的直接原因,但從觀念史上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分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條件。但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不斷被強化、深化的’。”
新文化運動無視華盛頓會議
民族主義解釋不了歷史事實
秦暉對金觀濤、劉青峰的研究表示認同,並加以申論。對於“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如果僅看“凡爾賽”,中國作為戰勝國幾乎一無所獲;但從這個體系的整體來看,由於“凡爾賽”的不公在“華盛頓”得到很大程度的糾正,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所得不僅是“大體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國當時的實際實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成功:
只要看看以當時中國經濟與軍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卻能在此後幾年裡先後收回青島、膠濟路、威海衛和原則上收回廣州灣,而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統一和國力相對明顯提高的條件下卻用了6年才收回旅順、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門,就能理解華盛頓會議的意義。再考慮到中國在一戰晚期才參戰,而且只派出了華工,並未實際參與作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提前”抗日和舉國大規模殊死戰鬥所付慘重代價而言,一戰後中國的所得應該說是很客觀了。
但在新文化運動中,尤其是其激進一翼對此卻完全沒有反應。由於後來從新文化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國共兩黨勢力都全盤否定北京政府,對這個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沒有給予“民族主義”的評價。所以,新文化運動對華盛頓會議的真正主流態度,與其說是批判,毋寧說是“無視”。
值得玩味的是,根據數據庫不同時期的數據顯示,已經被華盛頓會議糾正的巴黎和會,隨時間推移反而被備受重視,而糾正巴黎和會的華盛頓會議卻很快被“忘記”,不僅沒有讚揚,連批評都幾乎沒有了。而且,在華盛頓會議上西方已經改變了巴黎和會時的態度,此後中國遭受到的侵略(如“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基本都是來自蘇俄和日本,何以學習蘇俄而不再學習西方的“救亡壓倒啟蒙”卻仍然在繼續發展?所以,“民族主義”並不能解釋這些現象。
金觀濤、劉青峰對此評述說:《新青年》知識群體在頭幾年對十月革命“並不是特別用心”,因此與其說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使中國人知道了社會主義,毋寧說是接受社會主義才使國人聽進去了俄國的這“一聲炮響”,在知識分子愈來愈認同“社會革命”,乃至接受社會主義後,“才對十月革命愈來愈有興趣”。
十月革命
在秦暉看來,國人在列寧上臺四五年後“才對十月革命愈來愈有興趣”,並不是因為這幾年之後蘇俄對華外交愈來愈友善和平等,而是因為上述國人對蘇俄的社會改造和新社會模式愈來愈看好。
秦暉認為,變化的動力主要來自“啟蒙”本身,而不是來自“救亡”。不是因為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變得更大使中國的學習對象從西方轉向更為友好的蘇俄,進而學習目標也從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轉向了俄國式的社會主義,而是相反,由於國人啟蒙興趣轉向“社會革命”,導致中國人的“救亡”抗爭對象從俄國人那裡轉移,而集中對準了“西方”。
新文化運動並非第一次啟蒙運動
儒家思想才是近代啟蒙的內在動力
除此之外,秦暉認為,中國的思想啟蒙早在辛亥革命前幾十年就已經出現,並且不斷髮展,否則根本不會有辛亥革命。並且,秦暉在考察啟蒙思想史發現,學習西方的動力在於中國內部。在晚清時期,中國的先覺者從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出發,也就是從“孔孟之道”出發,對比中西現實之後,認為中國早已禮崩樂壞而“三代聖賢之世”見於西土。只是相對於中國過去的“儒表法裡”而言,中國那時的啟蒙主要是衝著“法裡”,而不是衝著“儒表”的,“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緒後,成為呼應“西學”的啟蒙動力。
由於後人錯把“啟蒙”與“反儒”畫上等號,才忽視了“第一次啟蒙”的存在。而實際上,也正是由於第一次啟蒙的推動,中國才有了衝著“秦制”、而不是衝著“孔教”而來的辛亥革命。所以,革命後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是第二次啟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啟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卻也是對上一次啟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偏移得愈來愈厲害。
在秦暉看來,這種“反法之儒”雖沒有存在“古典的憲政民主思想”,但“從道不從君”的古儒之風、以“民主”反極權,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嚴和人格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給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國提供了思想動力,併為接軌“西學”提供了本土資源。比如郭嵩燾歎羨西洋國政民風:“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由三代盛時之視狄夷也。”再如王韜所言,西洋“以禮儀為教”,“以仁信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有趣的是,郭嵩燾等都是清朝官員,洪仁玕則是反清的“粵匪”,但他們對西方的看法卻差不多。洪仁玕說,西洋“禮義富足”、“誠實寬廣,有古人遺風焉”。不僅如此,連朝廷的極端保守派官員都在私下“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比郭嵩燾等還要高調。
郭嵩燾
而這一切都是鴉片戰爭後、戊戌變法前,即新文化運動之前幾十年的事。郭嵩燾這些人當然不懂什麼“新文化”,他們其實還是傳統儒者,西方更未必真與“三代”相似,但是已經與西方比較,古儒心底潛藏的對“秦制”不滿就冒了出來。而崇信人性惡的法家拜服的是鐵腕賞罰、順昌逆亡的皇權,對皇上本人談不上真正的忠誠,無權的“虛君”難免牆倒眾人推。在秦暉看來,這就是中國沒有成功實行君主立憲、卻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據說也是西方的現實)推到“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亞洲第一共和國”的文化原因。
這些儒家先覺者把古儒“官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的“民本思想”與西學中民權優先、國權服務與民權的“民主”觀念結合起來,明確提出改革的目的是為老百姓的幸福和權益,“富國強兵”只是順帶的目標。他們甚至名言:不能善待老百姓、提高老百姓地位的“強國”很可怕。譚嗣同的《仁學》並未稱引西哲話語,但主張“先民主,後強國”。秦暉認為,這應該算是“人權高於主權”之觀點在中國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極端的表述。
但是,“秦制”在中國傳統中一直有來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質疑,在沒有可行的制度參照時,這種質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黃宗羲等人)固然流於烏托邦,有了這一參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隨著國是日非、國難日深、民生益艱、民怨益積,公開“歎羨”終於成了主流。
所以,秦暉認為,早在鴉片戰爭後不久,部分國人一旦瞭解“夷情”,西方的民主共和便與中國傳統古儒久被“儒表法裡”體制所壓抑的崇周仇秦情結一拍即合,使反“秦制”、學習“洋三代”的“引西救儒”思想逐漸發展起來。到了清末新政時,革命派固然鼓吹共和,立憲派絕大多數也主張“英國式憲政”。而革命派和立憲派兩派的區別主要就是“排滿”與否,而不是民主與否,這樣才有了辛亥革命之變帝制為共和。所以,秦暉認為,把“民主”說成是五四才“啟蒙”的東西,是不符合事實的。
▼ ▲
近期聽道講壇活動預告
活動時間:5月6日下午14:00
地址:北京 東方梅地亞3層 M劇場
▼▼點擊鏈接,即可報名。
http://www.huodongxing.com/event/33845697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