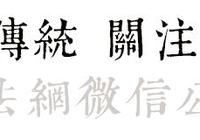被康有為譽為“榜書之宗”的《泰山經石峪摩崖》(習稱《泰山金剛經》)書法,是我國古代經典書法中的一朵奇葩,它以湛深的精神內涵,中和的審美特徵,兼容的形體和特異的筆法形式,最完整、典型地體現了佛文化的精義和中華民族書以載道的藝術宗旨。 自清代到民國,碑學的興盛使《泰山金剛經》的藝術價值為書壇所重新確認,考據家和書法家根據《泰山金剛經》的風格、體貌相較於山東鄒縣的四山摩崖書法,而不持太多異議的確定其為北齊時書,一時有安道壹為書者的推斷。北齊時的佛教尊崇和碑派書法興盛的人文條件,使《泰山金剛經》書法的產生有充足的精神依據和環境的支撐。《泰山金剛經》書寫內容為佛教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該經和《心經》一樣,統攝佛學大義,為佛教禪宗和其他一些宗派所持所本的佛祖慧論。是經詳論“不空之空”, 道 “無相之相”,以“是他、不是他、還是他”的中觀精義,說我、人、眾生、壽者相,說佛、說法、說心,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幻”總攬其要。這虛幻不是我們熟知的文化意義的“虛無”,而是以因果律作用於形色,以流轉意義而辨“色空”,進之以證形色成、住、壞、空的生滅本質,由是而類以“實”返“虛”,由“虛”轉“實”的宇宙萬物衍生規律。其書法所本經義如斯,書法的形跡和形跡所載的精神亦復如斯。《泰山金剛經》完全可以譽為完美體現佛教文化精神的天下第一書,其後世,只有弘一法師的書藝方可差強與其比擬。
《泰山金剛經》刊刻於泰山斗母宮上之山澗中,其字大逾尺,雍容偉岸的體態兼草情篆意,納隸楷特徵,其形體卓然實相,氣魄宏大,筆力雄勁,有視大山為土丘的氣度,有納百川而瀉海的襟懷。得此特點且推為極致,便易落入悍霸和狂躁的惡習中,但《泰山金剛經》的神妙正在於:雖大氣磅礴而又簡靜平和,雖體勢開張而雍容含蓄;以意象顯豁而得神理清明,以實相質樸而溢空寂虛靈。這諸多對立的審美取向被《泰山金剛經》巧妙地兼融,讓人面對其書頓生不可思議之感。品其書讓人感動而愈見親切,貽人信心而不施促迫,啟人心智而點化無痕,淨人心性而潤物無聲。難怪慧眼有自的人見《泰山金剛經》書法有晤對古佛之感,有混沌迷茫頓去之獲。
在中國書法裡,以實相證空靈必須有以下條件做支撐:
書者精神的自由和自在反映於書寫時心無掛礙的自然態上,這自然態作用於書,則體貌疏密聚散合自然之數(形生之理),它既窮盡變化以求異,又相互作用以形跡和神情的自然聯繫而求合(異合而演生形之則)故變化和諧的漢字形體和作用於形體意態的點畫始終和書者的精神相融無間地“流動”,使實相的書法形在自然態中通過自在的意趣和自由的精神拓展出虛靈的空間。
書法的點畫以充滿意機、意趣的筆力為基質,因力之用,書法點畫有向內而無限可讀的豐富。但力不能捨情、意而獨用,力之所出則情之所在,意之所行而力之以隨,它們應始終水乳不分地融合而用,故書法點畫以實為法,雖筆能扛鼎,逕取雄強和雄厚,亦可因情致、意韻、筆力的滲透而顯生動,生動則去僵滯和呆板,生動亦可於實相中見空靈。
複次,綜合前二者的因素作用於書之實相,復因漢字形體自具簡繁,因簡繁的配置而有點畫的輕重、疏密/精細、長短、參差的變化,故以實相為貌的書法,仍可在章法(全幅)、字法(單字結構)、筆法(作用於點畫形態)上體現出豐富的節律,這節律合於音律之理,故實相之跡亦可因變化律、對比律而得空靈的效果。
《泰山金剛經》正是渾化無跡地體現著上述特點,它的撼人的氣魄固與形體偉岸有關,但筆能扛鼎的結果亦使點畫產生三維深入,而有類似浮雕感的厚重,其厚重支撐書法形體更得蓄氣的寬厚,使內?L的筆意而生外拓的氣局。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泰山金剛經》並不看重今時或舊時文人書法在紙上慣用的乾溼、枯潤、散鋒、破筆等運筆效果,而善於藏頭護尾,筆筆中實,似乎減弱了體現毛筆筆性的運動感和筆痕的生動感,它沉酣以求的對點畫圭角的大力排斥,使點畫於寂靜中愈見肅穆。睹此而不解,這或許是人們對書法時間、空間運動的“定見”所致,《泰山金剛經》沉酣而靜穆的點畫有充沛的元神內實其中,有微妙而變化的筆致自然和諧的置陳於外,它的運動形式有如盈江春水,在看似平靜的表面卻有激越、酣暢的內動。緣於《泰山金剛經》書法的碑派歸屬和隸篆筆法的規定性,它以中鋒為筆法的主導形式,相對於晉唐行草書而言,它並不著意側鋒的使用和運筆的“八面用鋒”,它對中鋒的依賴(這種依賴並非我們今時認為的理性控制,它是書體表現的必須和意趣所主的自然反映,這反映是建立在斯時書寫的公共才能和書者獨特的控筆能力,以及興趣、意趣的獨特性基礎之上的。)和對點畫藏頭護尾的關注,使書中的任何一個點畫都與輕佻和油滑無涉。它對中鋒“疾澀”的嫻熟駕馭,使快而勢暢,澀而意蓄,有讀久彌濃的豐富韻致,而絕去清人常常掛懷以避的“中怯”現象。
形成《泰山金剛經》點畫形態的因素還有曲筆的大量使用,使轉用曲,且得“疾澀”之助,使《泰山金剛經》的點畫和使轉有神理的綿密和筆力的韌勁。同時,亦因用曲而使橫平豎直的筆畫更多意態和體勢上的變化。
北齊的時代條件決定了《泰山金剛經》字體風格上的包容性,它以書寫時代的文化給予為依憑,上溯隸篆,使形體主於隸楷的結字方法而出以篆書、隸書的筆意特徵,更因隸書雁尾的筆致時時快意書中,強化了隸書的主導傾向。三體交融而化合無痕,這對今時以書法形體求新者是頗具啟示意義的;把無類歸性的書體和審美通融性的對象雜糅或雜交,只能以削弱各自本有的特點和長處而告終,在中國書法史上,應該說鄭板橋的書風是可以說明問題的。而《泰山金剛經》的諸體兼融則可稱為成功的範例,因此它於形體上給人的創造性啟示也就多了一層現代意義。
不可否認,漫歷1400多年風雨的《泰山金剛經》已非斯時書丹、刻石的原初形態,換言之,它的形體和筆意因風化的因素已漶泐而不同程度地對原作有所改變,但大自然的神力所賦反而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和諧感和歷史感,以及因之而來的解讀上的多重可能.因其解讀上的非趨一性,才使有才能的書者有多種理解和切入的方便,因而形成取法相類而所獲不同的豐富性。
時代的演變使我們已失去產生《泰山金剛經》書法的人文條件,審美取向的轉移和書者知識結構的差異以及今時生態環境對人的精神狀態的強大左右力,使我們已難從更深層境上去理解《泰山金剛經》,可以印證的是清人對它的推重並未成為今時的推重,人們對渲洩以暢浮躁的藝術領受漸慣,對《泰山金剛經》書法的冷淡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因此,重新解讀和理解它就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工作。《泰山金剛經》書法給今世的啟示和教益並非僅在可供賞玩的形跡上,它更多的是提示了書道可資闡發的藝術內涵和人文精神,以及以書證道的人的終極關懷。
(本文為江蘇音像出版總社光盤及文字圖錄集之臨摹指要,後附有碑帖簡介和書家簡介)
(另結集出版於《明軒三集》之《翰墨因緣》周永健書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