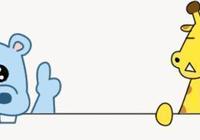“我認為制度在各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從未中斷悠久歷史的國家,路徑依賴的性質極其強烈。”北京大學教授汪丁丁在為布萊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寫推薦序時,意味深長地寫下這句話。在這篇文章裡,汪丁丁更多提到了作者阿瑟在學術思想領域上的開拓性精神,以及他的研究對於中國製度發展的深刻性思考。倘若我們不理解阿瑟在研究收益遞增理論時所經歷的排擠和孤立,我們就很難理解這位經濟學家對於自由思想的孜孜追求。倘若我們不理解制度強烈的路徑依賴性,我們就沒辦法更好地理解技術的本質——新技術是舊技術的一種新組合,所有技術都依賴於過去的技術。倘若我們從《技術的本質》裡只能讀出技術的本質,那麼我們就未能發現,這位野心勃勃而又獨特嚴謹的作者筆下那些對人類社會制度的深刻沉思。
學者的頭腦,哈耶克把它分為兩種,模糊型的和清晰型的。稍後,他補充了一個腳註,稱在寫《頭腦的兩種類型》這篇隨筆時,他未聽說過伯林對學者的劃分——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和知道許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認是一隻刺蝟。阿瑟也是一隻刺蝟,多年來,他跨越許多學科追蹤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課題,可稱為“路徑依賴性”。

▲布萊恩·阿瑟
阿瑟是1946年出生的,現在他被稱為經濟學家,而且在37歲時就成為斯坦福大學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這些都是事實,但不是全部事實。我清楚地記得在阿瑟1994年出版的《收益遞增與經濟中的路徑依賴性》一書開篇讀到這樣一則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學院做研究時,發現了經濟生活中存在強烈的收益遞增性並寫文章論述他的發現(我讀研究生時也讀他的這些文章)。那時他在斯坦福大學糧食研究所任職,可能還擔任生物系主任,他與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兩位核心人物共進午餐(聽上去是“求職午餐”),在他講述了自己的“收益遞增經濟學”之後,一位經濟學教授委婉地告訴他世界上沒有收益遞增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這位教授可能是當時的系主任,他告訴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遞增這回事,我們也不能承認它。這則故事,赫然寫在阿瑟著作的開篇。於是這部作品立即入選我的個人藏書——今天,我更樂意收藏電子版。
阿瑟1999年接受“領導力對話”採訪時也回憶了這段“痛苦如地獄”的經歷,他的描述是:在斯坦福大學的前十年,他發表了許多論文並擔任了系主任,然後,他用十年時間試圖發表一篇收益遞增論文,卻因此而離開了斯坦福大學。鼓舞他堅持探索的,是斯坦福大學校園最受愛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阿瑟說,阿羅幫助他獲得了1987年古根海姆獎學金,並引薦他去聖塔菲研究所任職。又據阿瑟1999年回憶,因新古典增長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MIT經濟學家索羅特意提醒聖塔菲研究所的主持人柯文,說他正在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因為阿瑟是無名之輩。

▲肯尼斯·阿羅,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羅始終為阿瑟的收益遞增經濟學大肆鼓吹,同樣深受阿瑟這一思想影響的,是因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史學家諾斯。我在香港大學教書時,於港大書店翻閱諾斯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運用阿瑟的收益遞增觀念於制度變遷的研究。我認為制度在各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從未中斷悠久歷史的國家,路徑依賴的性質極其強烈。從那時起,阿瑟成為我關注的西方學術核心人物之一。阿瑟的往事永遠提醒我,任何主流,包括經濟學主流,都不可避免地壓迫和排斥人類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為寫這篇中譯本序言,我檢索了網上關於阿瑟的報道和文章,我發現,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完全消失了。這些往事未必是被斯坦福大學別有用心地花錢“遮蔽”了,很可能是因為網絡社會的記憶原本就很短暫。
現在,我可以談正題了。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y),在制度經濟學獲得諾貝爾獎的那段時期,大約是1985—1995年這十年,對我們這些熱衷於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學者而言,真是一個最誘人的觀念。例如,張五常在諾斯得獎時對香港記者大呼“走寶”(即自家的寶貝被人家拿走了)。因為,據說,諾斯當年曾在華盛頓西雅圖校區聽張五常的新制度經濟學課程,這相當於師從五常呀。好事的記者於是去問諾斯怎樣評論張五常的“走寶”慨嘆。諾斯哈哈大笑,他的評論是,五常言之有理,可是他並未堅持這項研究。讀者懂得啦?五常教授20世紀70年代赴香港大學籌建經濟系, 1982年在芝加哥大學核心期刊《法與經濟學》雜誌發表了《企業的契約實質》(我評價為他畢生的登峰造極之作),此後,他的注意力轉向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再也無暇他顧。

▲張五常,知名經濟學家,代表作《佃農理論》
路徑依賴性,阿瑟的論述,諾斯的論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論述,可概括為這樣一項平凡的陳述:人的行為依賴於他們過去的全部行為。注意,是“依賴”而不是“由此被決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賴”。阿瑟早年研究人口學問題,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他發表的論文主要是人口學的。不過,他自幼最喜歡數學和工程學,在愛爾蘭的少年時代,他偶然選擇了電子工程專業,那時他不過17歲——“年輕得有些荒唐”。後來,可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我認為很可能是北美唯一一所最優秀的理論學院)時期,專注於收益遞增現象的研究。直到20世紀90年代主持聖塔菲研究所的“複雜性”課題組,自此以後,他主要研究經濟生活中的收益遞增現象。
技術,阿瑟指出,不是科學的副產品,而是或許恰好相反,科學是技術的副產品。古希臘人很早就懂得這一原理。亞里士多德說過,理論家的工作在於冥想,他們的模型是恆星系統,具有“永恆”這一基本性質。技藝是實踐者的工作,是一種關於偶然性的藝術,探求永恆原理的哲學家,不願為也。兩千年之後,技術仍是卑賤的實踐者的工作(例如米開朗基羅的工作),卻引發了近代科學。
阿瑟繼續考證,技術總是由一些基本的功能模塊組合而成的。最初的石器,打磨為兩類,鋒利的和有孔的,與手柄組合而成複合工具,例如“飛去來器”,例如“耜”與“耒”,例如“眼鏡”。凡技術發明者,首重適用性和便利性,發明專利所謂“實用新型”。這兩大性質要求使用新技術的人群將以往行為與新技術相合。如果你從微軟視窗系統轉入蘋果系統,你會有很多這樣的體會,多年之後,你試著適應微軟系統,又有很多這樣的體會。我們的身體(包括腦內的神經元網絡)可以記住我們的行為,並因記憶而有了行為的積累效應——貝克爾稱為“人力資本”。在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求學時,我聽一位人口統計學家告訴我,觀察人們早餐時吃的是哪一國的食物可準確判斷這些人來自哪一族群。她說,早餐習慣是最難以改變的,因為胃口或口味是“永恆的”。

▲道格拉斯·諾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諾斯有幾篇論文闡述制度的收益遞增效應。他指出,規模越大的政府總是追求更大規模,權力越大的人傾向於追求更大權力,成功的制度有複製自身的衝動,直到社會被鎖死於早已僵化但曾經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內。他還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類社會,作為“鎖死”效應的例證。諾斯的警告格外觸動我們這些中國學者,因為歷史太悠久而且太難以割捨,所以我們不能放棄傳統,但我們必須改造傳統,否則中國就可能消亡。

▲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2018年6月出版
於是,技術的本質,與制度的本質類似,因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性而常將人類“鎖入”既有的技術路徑或制度路徑。鎖入,於是可能鎖死。當社會被制度路徑鎖死時,社會消亡。當企業被技術路徑鎖死時,企業淘汰。現在,讀者可以翻閱阿瑟的這部作品了。
《技術的本質》一書已在精雕細課APP上線,聽作者布萊恩·阿瑟本人以及微軟加速器·北京CEO檀林為你講述~

本文作者:汪丁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研究經濟學思想史、行為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等前沿領域,著有《行為經濟學講義》、《經濟的限度》和《青年對話錄》系列等。
關於「聽好書」
「聽好書」是新東方旗下「精雕細課」APP的原創讀書欄目,由一批資深媒體人打造。精選“有品、有趣、有用”的好書,連接書與人,針對社會和人生問題,尋找解決之道,展開對話。
我們每週陪你精讀一本好書,通過專家學者的深度讀解,從書出發,打開生命的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