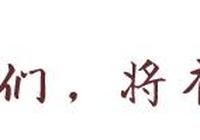來來回回的,我在這條路上走了十年。
這是西安東門外一條東西走向的路,然而很短,比例大一點的西安地圖上興許都找不到它的名字。
家在路東端的北側,辦公樓在路西端的南側。所以上下班對我來講,就是將這條路一次又一次地橫穿、縱貫。說起來只是簡單的重複,而重複得多了,就不再簡單。可以說,我對四季的感知、天氣的變換,對世俗的觀察、人情的瞭解,相當一部分,來自這條路上。
不止在平地走,我還能跳脫出這種平面的瑣碎和羈絆,在高處看。因為這十年裡,我搬了幾個辦公室,都是北向,都有足夠的高度。伏案之餘,或者有興致的時候,踱到窗前,一俯首,整條柿園路就在眼前。
一條街的市井生活雖然活色生香,但類似的場景,天天如是,厭倦是必然的。
所以更多的時候,我喜歡看東門,這也是在辦公室裡目之所及能看到的、整條柿園路上唯一百看不厭的東西。六百多年的一座古建築,在兩側高樓的圍堵下,依然穩重敦實、氣定神閒。蒼黑的屋頂,灰暗的牆面,一年到頭都是冬天的味道。一群褐色的鳥,應該是麻雀,從東邊飛過來,飛過整條柿園路,總會選擇在東門上落腳——老房子更接地氣吧。我從東門上城牆溜達的時候,常能看到麻雀,烏泱泱的一群,悠閒地跳躍覓食,唧唧喳喳地交流。
回頭,再說柿園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叫柿園路。西安的好多地名都有來歷,比如這條路周邊的雞市拐、長樂坊、景龍池、炮房街……然而柿園路沒有,翻了好多書,卻是找不到。想到小巷裡問那些蒼顏白髮的老者,看起來機靈一點的,或忙著打麻將,或忙著下棋,無暇回覆;看起來目光呆滯、口水長流的,你都沒有了問的勇氣。
就想,這條路的前生,應該是一片柿樹林,一片一片楓紅的柿葉,一枚一枚火紅的柿子,在過往的風中翻卷、端出。
然而好像與歷史不符。看民國,乃至明清時期的西安地圖,東門外這一片,是西安城牆以外最為繁華的地方,舊有所謂七寺八廟九學堂之說。從周邊的地名也可以看出:雞市拐是佔據一個街角的家禽交易市場,炮房街是製作鞭炮禮花的手工作坊群,更新街是接待進入西安府的官員暫歇、更衣之處……這樣一處市場繁榮、經濟活躍、市民高度聚集的所在,會有大片的柿樹林子存在嗎——觀賞價值和經濟價值都不高。
卻是不必深究了吧,這世上,有多少事,本來就不需要結果。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十年了,主要的工作就是寫材料。一天一天,永沒有寫完的時候。寫材料最熬人,常常加班到深夜,一個人沿著柿園路往回走。
應該是七八年前的夏天,行人絕跡,車輛稀少,兩側的店鋪都已經打烊,路燈光從樹叢裡一束一團地擠出來,那時道路中間還沒有隔離帶,整條柿園路顯得空曠迷離。一個流浪漢在馬路中間邊走邊唱,唱的是陝北的信天游,那種在黃土高原上瘋長起來的蒼涼謠曲,與這大都市的夜色格格不入,但他依然那麼痴迷地傾訴。看著他漸行漸遠,就想這樣一個漂泊的人吶,有著怎樣自由的內心和遼闊的思想。
又應該是五六年前的冬天,一場少見的大雪落過,片片輕盈的雪花竟能匯成沉甸甸的負擔,使得兩側的梧桐彎腰駝背;間有碩大的枝椏被壓折,空氣中充盈著清冽的氣息和新鮮的樹香。夜已深,空曠無人,前後顧盼,整條柿園路上只有我踩出一行深深的腳窩,忍不住伸開雙臂擁抱這嬰兒般純淨的夜空,莫名地就回到童年,回到大河之東的故鄉。
我想要說什麼——是每個早上一手捏著煎餅果子大口進食一手夾著各色行李擠上203路、37路、43路公交車行色匆匆的年輕人;是從來無視紅綠燈步履矯健強穿馬路到興慶宮公園鍛鍊的老頭老太太;是比他們都要早的穿著校服揹著雙肩揹包一路飛跑大呼小叫的孩子們;是春天和秋天的一掠而過夏天的酷暑難耐冬天的寒風掠過越來越擁擠的街道;是我在這條路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為生計奔波忙碌,並且無可挽回地衰老……
衰老的走向有兩個,死亡,或者新生。而唯心地理解,死亡何嘗不是一種新生。比如這座城市,從西周的豐鎬建都伊始,兩千多年的歲月一路走來,一次次地死亡,一次次地新生。比如柿園路,它最早成形,只是一條黃土小道,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再後來它鋪上了石子,墊上了黃沙,鋪上了柏油……一次次地死亡,一次次地新生。
作為這條路的一個過客,我的十年,對它只是彈指一揮間,而就在這十年間,無論工作多麼忙碌、滑稽、無意義,萬幸我還保留了對自由的渴望,對純真的嚮往,就像現在的每一個夜晚,柿園路上燈紅酒綠、人潮洶湧,車來車往,而我在其中,只要願意,我都能看見那位放聲高歌的遊子,我都能回到一河之隔的故鄉。
(來源:2018年09月01日西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