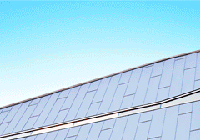一
2018年10月,我在上海一處街心公園小憩時,遇到一個瘦小的老太太。她蹲在地上準備貓糧,我很難不注意到她——一圈又一圈流浪貓把她圍在中間。
我被眼前貓山貓海的場景吸引,盯著看了她很久,直到她有所察覺,轉過頭來發現我,問我:“你喜歡貓咪嗎?逮一個回去。” 後來,我又接連碰到好幾次她在喂貓,才知道她叫張小桃。
69歲的張小桃,走起路來總是急匆匆的樣子。她樣貌普通,個頭很小,留一頭黑色短髮,時常穿素色立領襯衣,市面上早不時興的那種樣式,稍不注意,她就沒在市井人群中。
算起來,張小桃在這裡喂貓已經10年。這處街心公園公園面積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她在公司附近和家中也分別養著數十隻貓,零零總總加起來,她餵養的流浪貓將近100只。
上海是中國養貓最多的城市,市民們對這種軟萌的動物充滿了喜愛,數據顯示,全國十六分之一的貓都在上海。在這座巨型城市裡,貓咪填補了人們內心的空白,伴隨著繁衍生息。然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給人帶來的變動,使得很多貓失去了庇護。張小桃餵養的貓都是遭人遺棄,或者是野合產生的。
張小桃不是城市裡唯一的愛貓人,很多人像她一樣牽掛著這些城市縫隙裡的生活。一位用雞肉喂貓的中年女人說,張小桃很認真,“就像原來我們搞工作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貓,可能是書,也可能是別的。”一個附近的街坊聽聞我在記錄張小桃的故事,他告訴我,貓之於張小桃是一種執念,代表她在牽掛、但又不可能完全填補的東西。
喂貓這10年,張小桃沒有出過上海城。她是地道上海人,性格恬靜,不喜走動。哥哥姐姐都在城裡住,張小桃平日裡素少探望他們,年輕時結交的姐妹一個接一個退休,其他人時常結伴各地旅遊,只有張小桃不願出去。她需要喂貓。
一
2018年10月,我在上海一處街心公園小憩時,遇到一個瘦小的老太太。她蹲在地上準備貓糧,我很難不注意到她——一圈又一圈流浪貓把她圍在中間。
我被眼前貓山貓海的場景吸引,盯著看了她很久,直到她有所察覺,轉過頭來發現我,問我:“你喜歡貓咪嗎?逮一個回去。” 後來,我又接連碰到好幾次她在喂貓,才知道她叫張小桃。
69歲的張小桃,走起路來總是急匆匆的樣子。她樣貌普通,個頭很小,留一頭黑色短髮,時常穿素色立領襯衣,市面上早不時興的那種樣式,稍不注意,她就沒在市井人群中。
算起來,張小桃在這裡喂貓已經10年。這處街心公園公園面積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她在公司附近和家中也分別養著數十隻貓,零零總總加起來,她餵養的流浪貓將近100只。
上海是中國養貓最多的城市,市民們對這種軟萌的動物充滿了喜愛,數據顯示,全國十六分之一的貓都在上海。在這座巨型城市裡,貓咪填補了人們內心的空白,伴隨著繁衍生息。然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給人帶來的變動,使得很多貓失去了庇護。張小桃餵養的貓都是遭人遺棄,或者是野合產生的。
張小桃不是城市裡唯一的愛貓人,很多人像她一樣牽掛著這些城市縫隙裡的生活。一位用雞肉喂貓的中年女人說,張小桃很認真,“就像原來我們搞工作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貓,可能是書,也可能是別的。”一個附近的街坊聽聞我在記錄張小桃的故事,他告訴我,貓之於張小桃是一種執念,代表她在牽掛、但又不可能完全填補的東西。
喂貓這10年,張小桃沒有出過上海城。她是地道上海人,性格恬靜,不喜走動。哥哥姐姐都在城裡住,張小桃平日裡素少探望他們,年輕時結交的姐妹一個接一個退休,其他人時常結伴各地旅遊,只有張小桃不願出去。她需要喂貓。
作者圖 | 張小桃鏡頭下的流浪貓
張小桃離開過上海。18歲到28歲,她最好的年紀碰上了知青上山下鄉。張小桃插隊到了安徽,先是在大山裡勞作,然後調動到縣裡的國營工廠,擔當流水線的女工。等到返城回到上海,她已經是個大姑娘了。
如今,她再也不會離開上海,這100多隻流浪貓將她捆綁在了這座城市。上海放逐了這些貓,讓它們流浪四處,而她決定做點什麼。
二
1968年,是中國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潮的開端。那之後,上海城裡,有超過60萬年輕人被送出城外,輾轉到江西、安徽、雲南、黑龍江等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我趕上了一片紅。”張小桃說。那一年,張小桃臨近中學畢業,跟隨浪潮被送到了安徽農村。
蝴蝶就這樣煽了煽翅膀,抹去了張小桃原來的命運:她本應在前一年中學畢業,和離開上海的命運擦肩而過。
比她早一年中學畢業的同學,大都分配到了上海的工廠上班,最不濟的,也都留在上海,過著城市生活。張小桃望得見這些,她的時鐘只耽擱了一年,命運因此就走了截然不同的路。
1968年夏天,張小桃跟十幾名女知青搭火車到合肥,之後轉大巴到插隊的農村所在的深山旁,徒步穿過深山密林,在大山深處成了一名插隊知青。起先,張小桃哭了半個多月,她討厭那裡的閉塞,村民在她眼中淳樸卻無知:“他們連煤球都不知道,我就想著,以後從上海帶個煤球回來給他們看看。”
在安徽農村,她成了一個在全無生存技能的人。她每天硬著頭皮出工,不懂種田,連學挑擔都磕磕絆絆,掙的工分遠不夠餬口。那陣子張小桃給家人寫信報平安,寥寥幾句,最重要的是要錢:“一個工分只有1毛2,平日要向農民、供銷社買雞蛋、豆腐,不夠用。”沒有遠在上海的家人供養,她肯定熬不下去。
等到1972年,張小桃被縣城一處軍工廠選中,調出生產隊,成了機床車間裡一名流水線女工。雖然工廠也在山裡,但那是個全廠職工1000多人的大單位,這讓生產隊裡的知青們羨慕不已。同寢室的4個小姐妹特地從村裡搭車到工廠看她,在她的新宿舍住了一晚。張小桃招待她們去食堂吃了一頓。
短暫歡喜過後,張小桃重新回到日復一日的勞作中。瘦小的她成日與笨重的模具打交道,終於在一次更換一臺磨損的砂輪時,徒手搬運20多公斤的物料途中,不慎扭傷了腰。腰傷久治不愈,工廠只能調她去做不費體力的崗位——電話調度員,又同意她申請病假回上海治療。
回到上海,張小桃才知道,那個20多公斤的砂輪,造成她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末梢,連帶著,左小腿的肌肉有了萎縮跡象。
那時的世界在悄悄變化,政策鬆動後,公社的幾個小姐妹以知青身份陸續回了上海,在上海找到單位落檔、上崗。張小桃不同,她入職工廠時已算上崗職工。想回上海,她只能先退回農村恢復知青身份,又或者在單位等待退休。
沒有人教張小桃該怎麼做,退回知青再回上海,操作時間長,唯恐夜長夢多:“搞不好不僅丟了工作,還得一輩子在安徽的公社種地。”這麼一想,她不敢冒險,決定按兵不動。
眼見當初留在上海的同齡人、1974年到1975年間申請回滬的小姐妹,還有家中的兄姐都在上海有了各自的事業,張小桃漸漸變了想法——回到家鄉上海的希望渺茫。她開始一延再延病假,不想回到安徽工廠,彷彿在上海呆久了,她也能擁有與大家相似的前程。
期間,安徽的單位見她久病不歸,多次通知回安徽,“做個了結”。家裡人勸她接受現實,安穩在安徽工作到退休。1978年,28歲的張小桃最後一次坐火車去了安徽,以“身體喪失勞動能力”為由申請辦理了病退。
張小桃在28歲這年,成了那家工廠裡最年輕的退休職工,這是最快的辦法,也是最糟糕的辦法。
三
回到上海的第9年,張小桃的第一隻貓出現了。1987年,她37歲,尚且未婚,與母親、姐姐和哥哥同住。他們的家,是一棟三層老樓房,位於上海重慶南路和淮海中路交界,走到老弄堂深處便能尋到。
由於已經登記退休,回到上海後,張小桃再無法與任何單位形成勞動關係,失去辦理五險一金的資格,收入也一直在最低標準線上掙扎。
她輾轉於市井之中,在小商品市場當幫工,在郵局當過一段時間徵訂員。有段時間,她在家中一樓沿街開闢店面,拉朋友一起開了間麵館,她負責燒澆頭,生意不錯。
那隻貓就出現在張小桃開面館的時期。它原本是外甥女的寵物,小姑娘把它抱回家後,很快丟失了新鮮感,那隻貓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原本,那隻小貓應該被拋棄,加入上海街頭數以百萬計的流浪貓群。好在張小桃整日在家中,小貓就交給張小桃餵養,和被拋棄為流浪貓的命運擦肩而過。它尚未有名字,張小桃見它活潑,便取名“小老虎”,算是接納了它。
接納這隻小貓時,張小桃正處於心灰意冷的狀態。她愛上了一個上海男人,他有著跟她類似的遭遇,戶口也滯留外地,因著相似的時代際遇,張小桃感覺與他惺惺相惜。加上多年來她沒有戶口,打過多份工,對配偶是否有上海戶口,反倒沒什麼執念:“我覺得他脾氣很好,也會做裁縫,儘管沒工作但說不定能靠著餬口。”
張小桃帶男人回家,可母親和兄姐嫌棄對方沒有上海戶口,不同意他們結婚。張小桃拗不過家人,只能作罷。但兩人分手後,母親和小姐妹熱心給他介紹了多個“朋友”,條件都好,都有上海戶口。張小桃一一回絕了。
“小老虎”這時出現得恰是時候。麵館打烊,人群散去,張小桃鮮少出門,就窩在店裡休息。“小老虎”總喜歡跳到她膝蓋上,自顧自打盹睡著。知道她去燒貓食,“小老虎”便跟在她腳邊蹦來蹦去,歡喜得不得了。
“小老虎”總能消解張小桃的不快樂,張小桃難過時,它會焦急地對著女主人一通“喵喵喵”直叫。“我也忘記了,當時因為什麼事不高興。但看到貓,就覺得好多了。” 張小桃說。
擱淺的婚事,在張小桃40歲那年有了轉機。母親終於同意張小桃與那個沒有戶口的上海男人結婚。1999年,三層小樓所在的地塊拆遷,張小桃關了麵館,到郵局做了幾年徵訂員。直到今年69歲,她還在工作。
檔案中的張小桃,她在28歲那年退休,工齡永遠停留在9年,每月可分得2100元退休金。9年的工齡,遠遠不夠上海養老保險最低繳納年限,許多醫療保障內容也與她無關。她和上海的關係還是太淺了。
一
2018年10月,我在上海一處街心公園小憩時,遇到一個瘦小的老太太。她蹲在地上準備貓糧,我很難不注意到她——一圈又一圈流浪貓把她圍在中間。
我被眼前貓山貓海的場景吸引,盯著看了她很久,直到她有所察覺,轉過頭來發現我,問我:“你喜歡貓咪嗎?逮一個回去。” 後來,我又接連碰到好幾次她在喂貓,才知道她叫張小桃。
69歲的張小桃,走起路來總是急匆匆的樣子。她樣貌普通,個頭很小,留一頭黑色短髮,時常穿素色立領襯衣,市面上早不時興的那種樣式,稍不注意,她就沒在市井人群中。
算起來,張小桃在這裡喂貓已經10年。這處街心公園公園面積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她在公司附近和家中也分別養著數十隻貓,零零總總加起來,她餵養的流浪貓將近100只。
上海是中國養貓最多的城市,市民們對這種軟萌的動物充滿了喜愛,數據顯示,全國十六分之一的貓都在上海。在這座巨型城市裡,貓咪填補了人們內心的空白,伴隨著繁衍生息。然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給人帶來的變動,使得很多貓失去了庇護。張小桃餵養的貓都是遭人遺棄,或者是野合產生的。
張小桃不是城市裡唯一的愛貓人,很多人像她一樣牽掛著這些城市縫隙裡的生活。一位用雞肉喂貓的中年女人說,張小桃很認真,“就像原來我們搞工作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貓,可能是書,也可能是別的。”一個附近的街坊聽聞我在記錄張小桃的故事,他告訴我,貓之於張小桃是一種執念,代表她在牽掛、但又不可能完全填補的東西。
喂貓這10年,張小桃沒有出過上海城。她是地道上海人,性格恬靜,不喜走動。哥哥姐姐都在城裡住,張小桃平日裡素少探望他們,年輕時結交的姐妹一個接一個退休,其他人時常結伴各地旅遊,只有張小桃不願出去。她需要喂貓。
作者圖 | 張小桃鏡頭下的流浪貓
張小桃離開過上海。18歲到28歲,她最好的年紀碰上了知青上山下鄉。張小桃插隊到了安徽,先是在大山裡勞作,然後調動到縣裡的國營工廠,擔當流水線的女工。等到返城回到上海,她已經是個大姑娘了。
如今,她再也不會離開上海,這100多隻流浪貓將她捆綁在了這座城市。上海放逐了這些貓,讓它們流浪四處,而她決定做點什麼。
二
1968年,是中國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潮的開端。那之後,上海城裡,有超過60萬年輕人被送出城外,輾轉到江西、安徽、雲南、黑龍江等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我趕上了一片紅。”張小桃說。那一年,張小桃臨近中學畢業,跟隨浪潮被送到了安徽農村。
蝴蝶就這樣煽了煽翅膀,抹去了張小桃原來的命運:她本應在前一年中學畢業,和離開上海的命運擦肩而過。
比她早一年中學畢業的同學,大都分配到了上海的工廠上班,最不濟的,也都留在上海,過著城市生活。張小桃望得見這些,她的時鐘只耽擱了一年,命運因此就走了截然不同的路。
1968年夏天,張小桃跟十幾名女知青搭火車到合肥,之後轉大巴到插隊的農村所在的深山旁,徒步穿過深山密林,在大山深處成了一名插隊知青。起先,張小桃哭了半個多月,她討厭那裡的閉塞,村民在她眼中淳樸卻無知:“他們連煤球都不知道,我就想著,以後從上海帶個煤球回來給他們看看。”
在安徽農村,她成了一個在全無生存技能的人。她每天硬著頭皮出工,不懂種田,連學挑擔都磕磕絆絆,掙的工分遠不夠餬口。那陣子張小桃給家人寫信報平安,寥寥幾句,最重要的是要錢:“一個工分只有1毛2,平日要向農民、供銷社買雞蛋、豆腐,不夠用。”沒有遠在上海的家人供養,她肯定熬不下去。
等到1972年,張小桃被縣城一處軍工廠選中,調出生產隊,成了機床車間裡一名流水線女工。雖然工廠也在山裡,但那是個全廠職工1000多人的大單位,這讓生產隊裡的知青們羨慕不已。同寢室的4個小姐妹特地從村裡搭車到工廠看她,在她的新宿舍住了一晚。張小桃招待她們去食堂吃了一頓。
短暫歡喜過後,張小桃重新回到日復一日的勞作中。瘦小的她成日與笨重的模具打交道,終於在一次更換一臺磨損的砂輪時,徒手搬運20多公斤的物料途中,不慎扭傷了腰。腰傷久治不愈,工廠只能調她去做不費體力的崗位——電話調度員,又同意她申請病假回上海治療。
回到上海,張小桃才知道,那個20多公斤的砂輪,造成她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末梢,連帶著,左小腿的肌肉有了萎縮跡象。
那時的世界在悄悄變化,政策鬆動後,公社的幾個小姐妹以知青身份陸續回了上海,在上海找到單位落檔、上崗。張小桃不同,她入職工廠時已算上崗職工。想回上海,她只能先退回農村恢復知青身份,又或者在單位等待退休。
沒有人教張小桃該怎麼做,退回知青再回上海,操作時間長,唯恐夜長夢多:“搞不好不僅丟了工作,還得一輩子在安徽的公社種地。”這麼一想,她不敢冒險,決定按兵不動。
眼見當初留在上海的同齡人、1974年到1975年間申請回滬的小姐妹,還有家中的兄姐都在上海有了各自的事業,張小桃漸漸變了想法——回到家鄉上海的希望渺茫。她開始一延再延病假,不想回到安徽工廠,彷彿在上海呆久了,她也能擁有與大家相似的前程。
期間,安徽的單位見她久病不歸,多次通知回安徽,“做個了結”。家裡人勸她接受現實,安穩在安徽工作到退休。1978年,28歲的張小桃最後一次坐火車去了安徽,以“身體喪失勞動能力”為由申請辦理了病退。
張小桃在28歲這年,成了那家工廠裡最年輕的退休職工,這是最快的辦法,也是最糟糕的辦法。
三
回到上海的第9年,張小桃的第一隻貓出現了。1987年,她37歲,尚且未婚,與母親、姐姐和哥哥同住。他們的家,是一棟三層老樓房,位於上海重慶南路和淮海中路交界,走到老弄堂深處便能尋到。
由於已經登記退休,回到上海後,張小桃再無法與任何單位形成勞動關係,失去辦理五險一金的資格,收入也一直在最低標準線上掙扎。
她輾轉於市井之中,在小商品市場當幫工,在郵局當過一段時間徵訂員。有段時間,她在家中一樓沿街開闢店面,拉朋友一起開了間麵館,她負責燒澆頭,生意不錯。
那隻貓就出現在張小桃開面館的時期。它原本是外甥女的寵物,小姑娘把它抱回家後,很快丟失了新鮮感,那隻貓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原本,那隻小貓應該被拋棄,加入上海街頭數以百萬計的流浪貓群。好在張小桃整日在家中,小貓就交給張小桃餵養,和被拋棄為流浪貓的命運擦肩而過。它尚未有名字,張小桃見它活潑,便取名“小老虎”,算是接納了它。
接納這隻小貓時,張小桃正處於心灰意冷的狀態。她愛上了一個上海男人,他有著跟她類似的遭遇,戶口也滯留外地,因著相似的時代際遇,張小桃感覺與他惺惺相惜。加上多年來她沒有戶口,打過多份工,對配偶是否有上海戶口,反倒沒什麼執念:“我覺得他脾氣很好,也會做裁縫,儘管沒工作但說不定能靠著餬口。”
張小桃帶男人回家,可母親和兄姐嫌棄對方沒有上海戶口,不同意他們結婚。張小桃拗不過家人,只能作罷。但兩人分手後,母親和小姐妹熱心給他介紹了多個“朋友”,條件都好,都有上海戶口。張小桃一一回絕了。
“小老虎”這時出現得恰是時候。麵館打烊,人群散去,張小桃鮮少出門,就窩在店裡休息。“小老虎”總喜歡跳到她膝蓋上,自顧自打盹睡著。知道她去燒貓食,“小老虎”便跟在她腳邊蹦來蹦去,歡喜得不得了。
“小老虎”總能消解張小桃的不快樂,張小桃難過時,它會焦急地對著女主人一通“喵喵喵”直叫。“我也忘記了,當時因為什麼事不高興。但看到貓,就覺得好多了。” 張小桃說。
擱淺的婚事,在張小桃40歲那年有了轉機。母親終於同意張小桃與那個沒有戶口的上海男人結婚。1999年,三層小樓所在的地塊拆遷,張小桃關了麵館,到郵局做了幾年徵訂員。直到今年69歲,她還在工作。
檔案中的張小桃,她在28歲那年退休,工齡永遠停留在9年,每月可分得2100元退休金。9年的工齡,遠遠不夠上海養老保險最低繳納年限,許多醫療保障內容也與她無關。她和上海的關係還是太淺了。
四
張小桃的家,距離她喂貓的公園距離不到500米。那是一處公屋,面積並不寬裕,打開門便是廚房,挨著約兩平方米的衛生間,再往裡走,客廳極小,剩餘的空間被隔成兩件緊湊的臥室。兒子住稍小的一間,張小桃和丈夫的臥室稍大,放下一張沙發和一張小桌子後,便格外逼仄,在裡面走動不小心便會碰倒東西。
緊湊的屋子沒有擠壓出更為親密的家庭生活。張小桃性格寡淡,丈夫老張、兒子也是如此。張小桃到郵局工作後,丈夫也到外地謀生。孩子很長一段時間,都借住在張小桃姐姐家裡。
我問張小桃,自己大部分工資用來喂貓,也沒多想著孩子,會不會有些愧疚?張小桃輕描淡寫地回答:“不會,因為我為這個家勞動了,不會不好意思。”
後來她又給了我另一個答案:“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和老張年紀大了,他以後靠不了我們,早點知道生活艱辛,也好。”
2017年,張小桃的兒子從北京辭職回家待業,之後每天關在房間裡學習電腦繪圖與建模,說兩年後再回北京謀生,現在兩年已過,夫婦倆也沒有多問。
晚餐時間,兒子獨自在房內進食,夫婦倆窩在客廳一張小桌旁進食。幾無交流。張小桃更多時候邊夾動吃食,邊用平板電腦查看各類愛貓群和救助群的信息。她不時放下筷子,敲字回覆信息。
與收養來的7只貓咪相比,丈夫與兒子更像是局外人。
每個工作日上午接近11點,張小桃從家裡出來,走到街口等去往單位的公交車。
張小桃下車的地方距離黃浦江不遠,那是一棟上世紀90年代竣工的公寓大樓,看起來有些破敗。現在,張小桃就在臨街2層的證券公司當保潔員。
原本,張小桃一個人打兩份工,連帶證券公司相鄰公寓的保潔也一併包攬。兩座公寓大樓通過一條天井式的過道連接,過去,張小桃在天井裡收養了許多流浪貓。那時候業績景氣,證券公司的食堂時常留有剩飯,張小桃覺得浪費,便想辦法招呼附近的流浪貓來吃。
其實,招來流浪貓並不費力氣。上海這座城市的街頭,多的是無人看管的流浪貓。它們遊蕩在城市最為人忽視的空間,長時間處於飢餓、疾病與無主的狀態之中。長期以來,上海一直在試圖平衡這座城市與數量龐大的流浪貓狗的關係。
張小桃接管了其中的100多隻流浪貓。起初,在每個工作日傍晚,貓從下水道鑽進證券公司所在的大廈,吃貓糧,躲避風雨,在這裡睡覺。有隻患口炎的貓,張小桃特地給它留了一間挨著過道的辦公室,下班時留一個窗子,晚上貓咪跳進了睡覺,白天有人時就溜出去。
你問張小桃喂貓的理由,她只會告訴你:“捨不得貓咪沒有吃的。”為此,她堅持從每月並不多的工資裡省出錢來,購買99元每20斤的貓糧,餵養這些流落街頭的無主寵物。她記了帳,每月她需要耗費約230斤貓糧,花費近1140元。今年夏天,張小桃又打電話給姐姐,問能不能每月給她200塊錢:“喂喂貓咪呀。錢實在不夠了,你就當作作功德。”姐姐答應了。
即使在證券公司業績不景氣,食堂取消後,張小桃依舊無法拋下這些無主的動物。於她而言,它們並不只是消耗剩飯的工具。再沒有一種動物,像這些流浪貓一樣契合她前半生的經歷了。
它們的主人在上海城市化過程中不斷搬遷,當人類為維持體面自顧不暇時,不少人便顧及不上陪伴身旁的寵物貓。這些寵物因此流落街頭,成了上海擴大城市化過程中,被犧牲驅趕的部分。
一
2018年10月,我在上海一處街心公園小憩時,遇到一個瘦小的老太太。她蹲在地上準備貓糧,我很難不注意到她——一圈又一圈流浪貓把她圍在中間。
我被眼前貓山貓海的場景吸引,盯著看了她很久,直到她有所察覺,轉過頭來發現我,問我:“你喜歡貓咪嗎?逮一個回去。” 後來,我又接連碰到好幾次她在喂貓,才知道她叫張小桃。
69歲的張小桃,走起路來總是急匆匆的樣子。她樣貌普通,個頭很小,留一頭黑色短髮,時常穿素色立領襯衣,市面上早不時興的那種樣式,稍不注意,她就沒在市井人群中。
算起來,張小桃在這裡喂貓已經10年。這處街心公園公園面積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她在公司附近和家中也分別養著數十隻貓,零零總總加起來,她餵養的流浪貓將近100只。
上海是中國養貓最多的城市,市民們對這種軟萌的動物充滿了喜愛,數據顯示,全國十六分之一的貓都在上海。在這座巨型城市裡,貓咪填補了人們內心的空白,伴隨著繁衍生息。然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給人帶來的變動,使得很多貓失去了庇護。張小桃餵養的貓都是遭人遺棄,或者是野合產生的。
張小桃不是城市裡唯一的愛貓人,很多人像她一樣牽掛著這些城市縫隙裡的生活。一位用雞肉喂貓的中年女人說,張小桃很認真,“就像原來我們搞工作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貓,可能是書,也可能是別的。”一個附近的街坊聽聞我在記錄張小桃的故事,他告訴我,貓之於張小桃是一種執念,代表她在牽掛、但又不可能完全填補的東西。
喂貓這10年,張小桃沒有出過上海城。她是地道上海人,性格恬靜,不喜走動。哥哥姐姐都在城裡住,張小桃平日裡素少探望他們,年輕時結交的姐妹一個接一個退休,其他人時常結伴各地旅遊,只有張小桃不願出去。她需要喂貓。
作者圖 | 張小桃鏡頭下的流浪貓
張小桃離開過上海。18歲到28歲,她最好的年紀碰上了知青上山下鄉。張小桃插隊到了安徽,先是在大山裡勞作,然後調動到縣裡的國營工廠,擔當流水線的女工。等到返城回到上海,她已經是個大姑娘了。
如今,她再也不會離開上海,這100多隻流浪貓將她捆綁在了這座城市。上海放逐了這些貓,讓它們流浪四處,而她決定做點什麼。
二
1968年,是中國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潮的開端。那之後,上海城裡,有超過60萬年輕人被送出城外,輾轉到江西、安徽、雲南、黑龍江等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我趕上了一片紅。”張小桃說。那一年,張小桃臨近中學畢業,跟隨浪潮被送到了安徽農村。
蝴蝶就這樣煽了煽翅膀,抹去了張小桃原來的命運:她本應在前一年中學畢業,和離開上海的命運擦肩而過。
比她早一年中學畢業的同學,大都分配到了上海的工廠上班,最不濟的,也都留在上海,過著城市生活。張小桃望得見這些,她的時鐘只耽擱了一年,命運因此就走了截然不同的路。
1968年夏天,張小桃跟十幾名女知青搭火車到合肥,之後轉大巴到插隊的農村所在的深山旁,徒步穿過深山密林,在大山深處成了一名插隊知青。起先,張小桃哭了半個多月,她討厭那裡的閉塞,村民在她眼中淳樸卻無知:“他們連煤球都不知道,我就想著,以後從上海帶個煤球回來給他們看看。”
在安徽農村,她成了一個在全無生存技能的人。她每天硬著頭皮出工,不懂種田,連學挑擔都磕磕絆絆,掙的工分遠不夠餬口。那陣子張小桃給家人寫信報平安,寥寥幾句,最重要的是要錢:“一個工分只有1毛2,平日要向農民、供銷社買雞蛋、豆腐,不夠用。”沒有遠在上海的家人供養,她肯定熬不下去。
等到1972年,張小桃被縣城一處軍工廠選中,調出生產隊,成了機床車間裡一名流水線女工。雖然工廠也在山裡,但那是個全廠職工1000多人的大單位,這讓生產隊裡的知青們羨慕不已。同寢室的4個小姐妹特地從村裡搭車到工廠看她,在她的新宿舍住了一晚。張小桃招待她們去食堂吃了一頓。
短暫歡喜過後,張小桃重新回到日復一日的勞作中。瘦小的她成日與笨重的模具打交道,終於在一次更換一臺磨損的砂輪時,徒手搬運20多公斤的物料途中,不慎扭傷了腰。腰傷久治不愈,工廠只能調她去做不費體力的崗位——電話調度員,又同意她申請病假回上海治療。
回到上海,張小桃才知道,那個20多公斤的砂輪,造成她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末梢,連帶著,左小腿的肌肉有了萎縮跡象。
那時的世界在悄悄變化,政策鬆動後,公社的幾個小姐妹以知青身份陸續回了上海,在上海找到單位落檔、上崗。張小桃不同,她入職工廠時已算上崗職工。想回上海,她只能先退回農村恢復知青身份,又或者在單位等待退休。
沒有人教張小桃該怎麼做,退回知青再回上海,操作時間長,唯恐夜長夢多:“搞不好不僅丟了工作,還得一輩子在安徽的公社種地。”這麼一想,她不敢冒險,決定按兵不動。
眼見當初留在上海的同齡人、1974年到1975年間申請回滬的小姐妹,還有家中的兄姐都在上海有了各自的事業,張小桃漸漸變了想法——回到家鄉上海的希望渺茫。她開始一延再延病假,不想回到安徽工廠,彷彿在上海呆久了,她也能擁有與大家相似的前程。
期間,安徽的單位見她久病不歸,多次通知回安徽,“做個了結”。家裡人勸她接受現實,安穩在安徽工作到退休。1978年,28歲的張小桃最後一次坐火車去了安徽,以“身體喪失勞動能力”為由申請辦理了病退。
張小桃在28歲這年,成了那家工廠裡最年輕的退休職工,這是最快的辦法,也是最糟糕的辦法。
三
回到上海的第9年,張小桃的第一隻貓出現了。1987年,她37歲,尚且未婚,與母親、姐姐和哥哥同住。他們的家,是一棟三層老樓房,位於上海重慶南路和淮海中路交界,走到老弄堂深處便能尋到。
由於已經登記退休,回到上海後,張小桃再無法與任何單位形成勞動關係,失去辦理五險一金的資格,收入也一直在最低標準線上掙扎。
她輾轉於市井之中,在小商品市場當幫工,在郵局當過一段時間徵訂員。有段時間,她在家中一樓沿街開闢店面,拉朋友一起開了間麵館,她負責燒澆頭,生意不錯。
那隻貓就出現在張小桃開面館的時期。它原本是外甥女的寵物,小姑娘把它抱回家後,很快丟失了新鮮感,那隻貓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原本,那隻小貓應該被拋棄,加入上海街頭數以百萬計的流浪貓群。好在張小桃整日在家中,小貓就交給張小桃餵養,和被拋棄為流浪貓的命運擦肩而過。它尚未有名字,張小桃見它活潑,便取名“小老虎”,算是接納了它。
接納這隻小貓時,張小桃正處於心灰意冷的狀態。她愛上了一個上海男人,他有著跟她類似的遭遇,戶口也滯留外地,因著相似的時代際遇,張小桃感覺與他惺惺相惜。加上多年來她沒有戶口,打過多份工,對配偶是否有上海戶口,反倒沒什麼執念:“我覺得他脾氣很好,也會做裁縫,儘管沒工作但說不定能靠著餬口。”
張小桃帶男人回家,可母親和兄姐嫌棄對方沒有上海戶口,不同意他們結婚。張小桃拗不過家人,只能作罷。但兩人分手後,母親和小姐妹熱心給他介紹了多個“朋友”,條件都好,都有上海戶口。張小桃一一回絕了。
“小老虎”這時出現得恰是時候。麵館打烊,人群散去,張小桃鮮少出門,就窩在店裡休息。“小老虎”總喜歡跳到她膝蓋上,自顧自打盹睡著。知道她去燒貓食,“小老虎”便跟在她腳邊蹦來蹦去,歡喜得不得了。
“小老虎”總能消解張小桃的不快樂,張小桃難過時,它會焦急地對著女主人一通“喵喵喵”直叫。“我也忘記了,當時因為什麼事不高興。但看到貓,就覺得好多了。” 張小桃說。
擱淺的婚事,在張小桃40歲那年有了轉機。母親終於同意張小桃與那個沒有戶口的上海男人結婚。1999年,三層小樓所在的地塊拆遷,張小桃關了麵館,到郵局做了幾年徵訂員。直到今年69歲,她還在工作。
檔案中的張小桃,她在28歲那年退休,工齡永遠停留在9年,每月可分得2100元退休金。9年的工齡,遠遠不夠上海養老保險最低繳納年限,許多醫療保障內容也與她無關。她和上海的關係還是太淺了。
四
張小桃的家,距離她喂貓的公園距離不到500米。那是一處公屋,面積並不寬裕,打開門便是廚房,挨著約兩平方米的衛生間,再往裡走,客廳極小,剩餘的空間被隔成兩件緊湊的臥室。兒子住稍小的一間,張小桃和丈夫的臥室稍大,放下一張沙發和一張小桌子後,便格外逼仄,在裡面走動不小心便會碰倒東西。
緊湊的屋子沒有擠壓出更為親密的家庭生活。張小桃性格寡淡,丈夫老張、兒子也是如此。張小桃到郵局工作後,丈夫也到外地謀生。孩子很長一段時間,都借住在張小桃姐姐家裡。
我問張小桃,自己大部分工資用來喂貓,也沒多想著孩子,會不會有些愧疚?張小桃輕描淡寫地回答:“不會,因為我為這個家勞動了,不會不好意思。”
後來她又給了我另一個答案:“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和老張年紀大了,他以後靠不了我們,早點知道生活艱辛,也好。”
2017年,張小桃的兒子從北京辭職回家待業,之後每天關在房間裡學習電腦繪圖與建模,說兩年後再回北京謀生,現在兩年已過,夫婦倆也沒有多問。
晚餐時間,兒子獨自在房內進食,夫婦倆窩在客廳一張小桌旁進食。幾無交流。張小桃更多時候邊夾動吃食,邊用平板電腦查看各類愛貓群和救助群的信息。她不時放下筷子,敲字回覆信息。
與收養來的7只貓咪相比,丈夫與兒子更像是局外人。
每個工作日上午接近11點,張小桃從家裡出來,走到街口等去往單位的公交車。
張小桃下車的地方距離黃浦江不遠,那是一棟上世紀90年代竣工的公寓大樓,看起來有些破敗。現在,張小桃就在臨街2層的證券公司當保潔員。
原本,張小桃一個人打兩份工,連帶證券公司相鄰公寓的保潔也一併包攬。兩座公寓大樓通過一條天井式的過道連接,過去,張小桃在天井裡收養了許多流浪貓。那時候業績景氣,證券公司的食堂時常留有剩飯,張小桃覺得浪費,便想辦法招呼附近的流浪貓來吃。
其實,招來流浪貓並不費力氣。上海這座城市的街頭,多的是無人看管的流浪貓。它們遊蕩在城市最為人忽視的空間,長時間處於飢餓、疾病與無主的狀態之中。長期以來,上海一直在試圖平衡這座城市與數量龐大的流浪貓狗的關係。
張小桃接管了其中的100多隻流浪貓。起初,在每個工作日傍晚,貓從下水道鑽進證券公司所在的大廈,吃貓糧,躲避風雨,在這裡睡覺。有隻患口炎的貓,張小桃特地給它留了一間挨著過道的辦公室,下班時留一個窗子,晚上貓咪跳進了睡覺,白天有人時就溜出去。
你問張小桃喂貓的理由,她只會告訴你:“捨不得貓咪沒有吃的。”為此,她堅持從每月並不多的工資裡省出錢來,購買99元每20斤的貓糧,餵養這些流落街頭的無主寵物。她記了帳,每月她需要耗費約230斤貓糧,花費近1140元。今年夏天,張小桃又打電話給姐姐,問能不能每月給她200塊錢:“喂喂貓咪呀。錢實在不夠了,你就當作作功德。”姐姐答應了。
即使在證券公司業績不景氣,食堂取消後,張小桃依舊無法拋下這些無主的動物。於她而言,它們並不只是消耗剩飯的工具。再沒有一種動物,像這些流浪貓一樣契合她前半生的經歷了。
它們的主人在上海城市化過程中不斷搬遷,當人類為維持體面自顧不暇時,不少人便顧及不上陪伴身旁的寵物貓。這些寵物因此流落街頭,成了上海擴大城市化過程中,被犧牲驅趕的部分。
作者圖 | 公園一角的流浪貓
五
每過一段時間,公園的草叢裡就會有小奶貓探出頭來,那是流浪貓又生崽了。
為了減緩這些出生即顛沛的生命的誕生,最近幾年,張小桃開始將流浪貓抓去做絕育手術。然而,比起自然繁衍與人為遺棄的速度,張小桃的絕育計劃如西西弗搬動石頭般徒勞。
張小桃最怕碰到路邊單獨擺放的紙箱。多年過來,她知道里面大多裝著被遺棄的寵物,她們最終都成了流浪貓。
有一天,張小桃又在公園裡撿到一方紙箱,裡面是隻“品種貓”。她想不通為何這樣的貓也會遭到遺棄,只覺得這隻小美短還有免於流落街頭的希望,便抱著盒子,沿街一戶戶問鋪主和路人:要不要領養這隻小貓?
家人希望她不要在流浪貓身上花這麼多心思,周遭的人變著法勸阻她,路過的陌生老人看她辛苦喂貓,關心她說:“自己也要照顧好身體啊。”張小桃不客氣地說:“你不要管!”在安徽一起下鄉的姐妹們說,張小桃在流浪貓身上找到了慰藉。
學佛的朋友告誡她:“太過親近流浪貓,以後會去畜生界”。張小桃不知道這輩子過成這樣,還能通過怎樣的方法獲得好命,餵養好這些貓,行善積德,或許下輩子就能生在一個好人家裡。
最後,她在一家咖啡店為那隻名貴貓找到了主人。“終於得救了一隻。”張小桃說。那她時常記掛這隻與顛沛的命運擦肩而過的小貓,每次經過咖啡店,都會特意看一眼它在不在店裡。
*本文中張小桃為化名
-END-
作者丨趙景宜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真實故事計劃】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