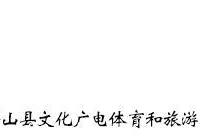「鐵號」走進柴達木
【鐵號】走進柴達木
原創:張怡華 鐵道兵公眾號 2018.10.4

柴達木,藍天白雲,交相輝映。戈壁雪山,厚重蒼莽。一一題記
此次遙遠的柴達木之行,我是揣著心事而來。 汽車沿青藏鐵路一直向西。過剛察、哈爾蓋、天峻……偶爾有人會問:“有了嗎?” “還好,你有了嗎?” 此時,我們說“有”的那種東西,叫做“高原反應”。 沒有想到,翻越海拔3847米的關角山,就覺得頭暈腦脹,隱隱作痛。我知道,這是高原反應。我暗地裡譏笑自己,一位曾經在青藏線上戰鬥過的老兵,現在怎麼就嬌氣了。 剛到青海那年,我不足二十歲,血氣方剛。現在呀,真是老咯! 我2007年內退,10年裡我3次重走青藏線,有人說,你傻。我說,你們不懂。因為我的青春足跡曾經在雪域高原停留,就像初戀情人,令我一生回望,又像是條搏動的血脈,連接著我的高原情伓。因為青藏鐵路不是一般的路,是用軍人的鮮血和生命鋪就而成,如果沒有這條暢通的動脈,青海和西藏就不會有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

抵達烏蘭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次日一大早醒來,又吃了些抗擊高原反應的藥丸,頓覺神清氣爽,好不欣喜。剛洗漱完,復員後在烏蘭縣城定居的張富有打來電話,他在城西花圈店門口等著我們。來到酒店大廳,看見外面正下著大雨。說也奇怪,昨晚還看了天氣預報,沒說今天有雨,怎麼就下雨了呢?看來今天要冒雨前往陵園了。真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風,悽悽切切,撲面而來。 掩映在蒼松翠柏中的烏蘭縣烈士陵園,長眠著近百位為解放烏蘭、建設烏蘭而犧牲的英烈們。陵園右邊的墳塋墓碑上都刻上了“鐵道兵”三個字,他們是當年為修建雪域天路而犧牲的戰友,大理石墓碑上雕刻他們的姓名、部隊番號、犧牲時間。他們的名字緊貼著金色柴達木,陪伴他們的是墓碑上那用鮮血染紅的閃閃紅星,還有那千年不沉的一鉤孤月。月沉月起,日升日落,年復一年,護佑著他們為之奮鬥終生的雪域天路。 雨中的花崗岩地面玉潔冰清,其中一塊墓碑上赫然雕刻著候宏生的名字。墓誌銘上寫著:候宏生,原89350部隊鐵道兵,湖南澧縣人,1972年12月入伍, 1975年4月13日修建青藏鐵路不幸犧牲。 秋風秋雨秋水,悲哀悲涼悲傷。才入立秋,就讓年過花甲的我們,再次領會了8月高原的寒意。高原高寒,就象一對雙胞胎,高了必然寒,高處不勝寒。 香燭在風中搖曳,香火在空中飄蕩。楊耀恆告訴我們:候宏生是和他一起從湖南桃源紡織印染廠入伍的,新兵連在一個班,新兵訓練結束後他去了10連任理髮員。1975年4月13日,部隊組織軍事訓練,本來連部勤雜班沒有安排訓練,他向連長請求參加演習,因炸藥包提前引爆,他和一個雲南排副不幸負傷。從桃源入伍的周繼凡當時是團長警衛員,當傷員抬上救援嘎斯車,他也爬上嘎斯車參與護送,救護車還沒到達師醫院,候宏生就停止了呼吸。回憶起當時救援情景,作為老鄉,周繼凡依舊心有餘悸。 宏生犧牲前的那個星期天,6連李慶和帶了一包油炸花生米去10連。宏生找來幾個老鄉相聚,又從地火龍火牆邊摸出兩瓶青稞酒。酒被均勻地傾倒在兩個刷牙用的搪瓷缸裡,搪瓷缸相互傳遞著,彼此間碰得山響,你一口我一口地幹了起來。宏生不喝酒,喜歡抽菸,那天破例地喝了幾口。帶著醉意,當兵三年了的老鄉們說起了心裡話。 有人說,高原當兵,太苦。 也有人說,能入黨就復員。 宏生和平常一樣樂觀開朗,笑容燦爛,他說他“喜歡當兵,羨慕四個蔸的軍裝。”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接著他又補充道。 說起戈壁灘中的那段搪瓷缸碰得山響,快樂“乾杯”的往事,如今家住長沙的李慶和戰友依舊記憶猶新。

柴達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四周被崑崙山、祁連山和阿爾金山脈所環抱。這裡氣候乾燥,環境惡劣,一年只刮一場風,從春刮到冬。雖然艱苦,四個蔸軍裝即幹部服,不僅是宏生,也是我和眾多戰士的理想和追求。 高原鐵道兵施工環境和生活條件很差,連裡幹部住的是乾打壘土坯房,房頂是油毛氈上枯草抹黃泥,非常簡陋。戰士們住的是帳篷,帳篷由鐵架組合而成,便於“志在四方”的鐵道兵們轉戰新的戰場。床鋪很窄,偶有新兵在睡夢中從上鋪掉下來。高原寒冷,一年有多半時間需要燒火取暖,帳篷門口築有火爐,火爐下面是個深坑,既是出煤灰也是傾倒洗臉水的地方,地火牆從下鋪下面通往帳篷後面的煙囪。 木裡煤礦,我是去過的,為了連隊生活及冬季烤火用煤,連裡派我們班去木裡跟車,煤礦沒有裝卸工,裝煤由連隊派人隨車裝運。大概是1976年11月上旬,連裡安排我帶4個人去木裡煤礦拖煤。從察汗諾出發時,凜烈的寒風中飄著星星點點的雪花,過二郎洞、關角隧道,沿途高原風光、萬里雪飄,充滿了詩情畫意般的景象。從天峻到木裡煤礦,沿途人煙罕至,公路坑坑窪窪,早己被大雪覆蓋,汽車湮沒在了茫茫風雪中,司機小心地看著前面的車道,憑記憶前行。 1977年2月24日,汽車連周躍全奉命率5臺車前往木裡煤礦拉煤。周躍全,1971年四川潼南兵(現為重慶潼南),去年回家探親,親朋好友為他介紹了對象,女孩在供銷社工作,計劃今年不復員就請探親假回家結婚。出車前,連長特別強調,天寒地凍出車,要特別注意安全。 出木裡煤礦,要翻越一座山坡。山坡其實並不高,公路順山勢而修,盤旋而上,最大的問題是,路面裡高外低。此處曾多次翻車,被司機們稱為鬼門關。時值嚴冬,天寒地凍,冰雪覆蓋著路面,車在盤山路的最險路段突然熄火,一熄火車就往後打滑,當滑到山坡邊時車還是剎住了。當時有戰友建議,將車上煤缷掉,減輕重量,由另一輛車用鋼絲繩拉住同時起動發動機。周躍全認為,卸煤裝煤太耗體力,在汽車的兩個後輪下墊上兩件皮大衣,可以增加摩擦力,車輛應該能安全起動。同時又將跟車的倆個戰友的叫下車,當他點火發動後,汽車直接滑向了百米多深的山溝裡。 拉著周躍全同志的遺體,車隊連夜返回,看到周躍泉同志遺體,戰士們哭了,哭得很傷心。甘肅籍張連長看到很多人在流淚,哽咽地說道,戰爭年代要是死人了,像你們這樣哭能行嗎?就這樣,戰友們頂著凜冽寒風,守在躍全靈前,黙黙地度過了那悲傷的夜晚。 整理遺物時,戰友們在周躍全的挎包裡看到了一個紅色筆記本,扉頁上寫著“革命方知友誼貴,分別倍知戰友親” 的離別贈言,這是老兵復員時送給他的筆記本,筆記本里有兩張照片,一張是他和對象的彩照合影,是用彩筆凃畫的,靦腆青春,一張是姑娘的單人照,清秀亮麗。40多年了,周躍全戰友靜臥在烏蘭烈士陵園,我在心裡輕輕地問道,躍全戰友,你在那邊還好嗎? 陵園裡並列排著於秀麗、康秋傑倆位戰友的墳冢,墓誌銘上顯示,她倆是原鐵道兵48團女兵,1970年12月入伍,1974年6月19日在執行任務時光榮犧牲,犧牲時年齡都是18歲。她們的年齡,永遠定格在了18歲的花季青春。



關於柴達木的荒涼;關於高原、高寒、強烈的紫外線;關於汽車失事;關於感冒而死亡的故事……有過高原經歷的人,都能講述很多,信手拈來。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無法想象在那種嚴酷的自然條件下,人的生命力是何等的脆弱。我承認,我是一個意志不堅定者,面對艱苦,我選擇了逃避,北京昌平籍王希正指導員曾幾次勸我留下,看我復員決心堅定,在退伍前兩個星期,才解決了我的組織問題。如今憶起那段軍營往事,雖然只當了四年兵,於我,是一輩子的青春記憶。因為我的青春曾經在柴達木的戈壁灘上逗留,曾經是天路的築路人。 雨停了。天空,烏雲依舊疊著烏雲,彷彿隨時會垮下來似的。站在陵園外面的公路上,仰望聳立在烈士陵園廣場上的“革命烈士紀念碑”, 心情還是沉浸在往事的記憶中。這是我復員後第三次來柴達木,看望我長眠在雪域高原的戰友們。可是,僅僅給你們獻上一個花圈,似乎還缺少點儀式感。 對!讓我們給你們敬個軍禮吧! 我平復了一下心情,放下揹包,理了理著裝,用手捋了捋稀疏的白髮,見路上來往車輛少了下來,招呼同來的汪中嶽、楊耀恆、周繼凡、王貴昭、張富有等6位戰友一齊走到公路中間,朝著陵園方向,我們以軍人的標準姿態,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6位老兵緩緩地舉起了右手:親愛的戰友們,你們還好嗎?我們看你們來了!我們以一位老戰士的名義,向你們敬禮!親愛的戰友們,請原諒我們,以後可能不會再來了,如今,我們也是快“奔七“的老人了,身體不允許我們再來。還記得嗎?當年烏蘭是我們都非常喜歡的地方,因為城裡有照相館,有商店,還有臉上有 “高原紅”的姑娘……烏蘭縣這些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青藏鐵路也早已通車了,想必在天堂的你們也看到了,你們也很高興吧?也許你們今天也來這裡了。剛才,我看到烏雲重疊的天空中露出了絲絲亮光,亮光刺破雲層,耀眼奪目,就像一雙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著我們,那不會是你們的眼睛吧?如果是你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公路中間不知站了許久。轉過頭來,看到的一幕讓我們驚呆了。原來,在我們的左右兩頭已有多輛汽車排成了長隊,他們竟然沒有鳴笛。我們趕緊讓開,歉意地看著前車司機。讓我們感動的是,司機那善意的目光,讓我看出他並無責備之意,過了好幾秒鐘,汽車才緩緩啟動,路過我們身邊時,長長地鳴著喇叭。我懂了。剛才,他們也與我一起向那些為青藏鐵路建設付出生命的戰士們致敬…… 張怡華2018年9月27日於官莊


鐵道兵公眾號第2018-356-1期
來源:信息中心
編輯:心寬無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