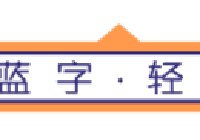文 │ 特約撰稿人 聆雨子
編輯 │ 夏天
榮譽拿到手軟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羅馬》,終於在內地公映。
就頒獎季裡的學院派審美而言,它在各個角度上都具備一個“優等生”的品相:大歷史、小人物、日常生活裡的奇觀性、女性視角、底層視角、拉丁美洲、少數族裔,每一項都是知識分子最熱衷討論的話語場。但是,對於普通觀眾,它並不算十分友好:且不說那些隱藏極深的寓意符號,或者水乳交融到難於分辨的現實和幻象,單單是“上世紀70年代的墨西哥社會到底正在經歷什麼”這類歷史背景,也很難存在於多少人的知識庫存當中。

所以,它似乎從頭至尾並沒引發太多熱議度,有興趣的觀者,三個月前都已經看過了,沒興趣的觀者,也無從被激起新的興趣。即使專業影評人們,也頗有一些對它的形式大於內容,給出了委婉的批評。那麼,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
被“性別敘事”稀釋的“社會敘事”
《羅馬》啟幕於一個極為帶感的開場:女僕在沖洗地板,一汪水漬的泡沫裡,映出天空中一架飛機緩緩掠過。從容和憂傷、變與不變、靜止或流動,盡在其中,言有盡而意無窮。
黑白影像的特有感光質地,還原了屬於夏天午後的慵懶和疏淡,長日空寂、歲月靜好,塵世間一切看似平穩如常,背影裡卻正在悄然孕育和駛出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時代。就像這個看似兒女雙全、夫妻和睦的中產之家:漂亮寬敞的房屋裡,好像總是雜物堆疊、收拾不乾淨;光可鑑人的地上,卻永遠灑滿狗屎;男主人氣派的蓋勒西汽車,總是與車庫碰撞刮擦、格格不入。

一切都很不錯,一切都有問題,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就會爆發。這是這個國、這個家、這群人,三位一體的命運同心圓。
女僕克萊奧,出身貧寒的印第安裔,辛勤勞作,有一個情人費爾明——同樣來自底層的、熱衷好勇鬥狠的無業遊民。僱主索菲亞,體面的精英階層,衣食無憂,有一個丈夫安東尼奧——談吐優雅、收入殷實的著名醫生。就在這樣一組鏡像關係裡,以雙線並行結構,緩緩展開了一場“兩個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女人”的相互對照,讓她倆同時遭遇著各自的劫數。
“女僕與主人的關係”也是電影史上常見的題材,只不過,有些作品偏重於描寫對立和反抗,比如表現黑人女傭所遭遇不公對待的美國電影《幫助》,有些作品則以信賴與彼此關懷為重心,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桃姐》。

至於《羅馬》,乍一看,它好像介於兩者之間:克萊奧從一出場就已經扮演著孩子們最大的精神依賴,唱著歌謠哄他們入睡和起床,有條不紊地安排和打理他們一整天的生活,聽取和分享他們的每一種小心思和小煩惱,這種存在感,幾乎是那對忙碌的父母所無法提供的,於是當一家人看電視時,她會情不自禁地坐在孩子們身邊、孩子們會情不自禁地摟住她(而不是母親),在這些情境裡,沒有人懷疑過她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
但是,克萊奧與女主人索菲亞的關係依然比較敏感和微妙,當後者盯著她幹活刷地、監督她是否及時關燈、抱怨她的清掃成果、責怪她沒能阻止孩子們的偷聽時,她們置身於某種一目瞭然的不對等當中。
這也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本片來自導演的童年回憶,那家庭向的“溫煦感”無疑構成了它的基色;既然影片自帶一種“以具體人物透視整體社會”的野心、又以1968-1971墨西哥革命為幕布,階級性的“對立感”也註定是它無從迴避的問題吧。
事實上,影片似乎一直在這種“溫煦感“和”對立性”之間搖擺著:在度聖誕的鄉村,原住民毒死了白人的狗;買嬰兒床的路上遭遇的街頭屠殺;傭人和狗始終住在大屋之外的邊緣空間裡……在這些時刻,“對立性”呼之欲出,但很快,它們又會被更大的“溫煦感”悄然覆蓋和淹沒:克萊奧和索菲亞有節制地和睦相處,等級分明地各司其位,心照不宣地彼此傲慢。

一直到她們陷入了完全相同的困境和考驗——她們都被各自的男人遺棄了。虛偽的安東尼奧和色厲內荏的費爾明,前者的“去趟加拿大”和後者的“去趟洗手間”,成為了背棄愛侶時殊途同歸的謊言,他們來自截然不同的階層,卻一樣讓人生厭。
被丟下的只有女性,索菲亞還帶著四個兒女,克萊奧還拖著懷孕之身。於是,她們開始彼此依偎、彼此搭救、彼此療傷。她們互訴衷腸、傾聽彼此的悵惘。她開始接納她參加家庭會議,帶她去海邊度假。
而她救下了風浪中的孩子,並向她和盤托出內心最深的隱祕:她一度不希望肚子裡的孩子活下來——這個隱祕,她不曾和朋友說,不曾和母親說,卻告訴了曾經對她並不算友好的女主人。“有困難大家一起度過,手拉手,肩並肩,對嗎?克萊奧。”到這一刻,故事已經足夠感人。但是,好像缺了一點什麼?剛剛提到過的“階級性”呢?“社會問題”呢?

當索菲亞對克萊奧講出“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做女人的總是孤身一人時”,命運已經既不和其所置身的社會層級成正比(“衣食足方能知榮辱”),也並不成反比(“為富不仁”),命運好像只跟性別相關。她們忽略了主僕身份、她們結成了精神共同體,因為她們意識到了彼此都是女人,而這一切的前提只是:她們都遇到了渣男。
這瞬間變成了一個八點檔的倫理道德故事,它好像再也無法和剛剛行將展開卻又消失無蹤的“上世紀70年代的墨西哥“建立聯繫,它好像可以發生在任何環境裡、任何時間點。
國家的激變帶來了人心的激變,人心的激變造成了愛與家庭的激變,愛與家庭的激變燭照出國家的激變,上述這個邏輯閉環,在這個開頭裡就已經初步奠定,這也應該是導演所預期的、這部電影最理想的主題形態。
只不過,在實際的表達中,性別視角跨越或者說調和了階級視角,我們沉浸於愛與家庭的激變,以此治癒了人心的激變,最終躲開了國家的激變。只是,當你沉醉前者的氛圍和影調時,是否也會遺憾於不曾到達後者的深刻與厚重。這,大約就是“形式大於內容”的起因與徵象。
被“自傳性”稀釋的“共情性”
不可否認,《羅馬》擁有著非常迷人的影像語言。
“羅馬”是主人公一家所在街道的名字,這個墨西哥市中心的社區地標命名了這部影片,所以它似乎天然就該是群戲、該是歷史的初稿和浮世繪。所以攝像機一直在以拉開卷軸畫般的方式橫移,而不是導演曾經習慣的運動長鏡頭(這在《地心引力》裡曾讓人無限驚豔)。
度假時遭遇的森林失火、操場演練、街頭的暴亂、醫院生產、在海中救助孩子,一直波瀾不驚的畫面裡,穿插了這樣五場紛擾動盪、充滿不安感的大戲,而它們,幾乎同步對應於克萊奧的內心變遷:憤怒、恐慌、躁動、痛苦、以及放下心結的自救。

從一次次跪趴在小院的地板上清理狗屎,到一步步走向汪洋裡的驚濤,從清潔劑的泡沫到大海的巨浪,女主與她的主人一家,共同走出了曾經困厄於中的狹小處境,實現了精神上的涅槃。還有那些俯拾皆是的符號和隱喻:前文提到的汽車與飛機、安東尼奧的戒指、費爾明的外衣、嬰兒、槍與棍棒。
然而,這些影像語言裡,似乎總缺了些細膩的情感流動。一種表面化的情緒和文本的單薄感,無處不在。自傳題材一旦涉及兒時回憶,往往會讓使用第一人稱的導演沉溺其中、無法自拔——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馮小剛的《芳華》,都是其中典型。
然而,也頗有一些作者反其道而行,冷靜剋制,帶著一種“就不想讓你看出我的感動”之執拗,侯孝賢拍攝《童年往事》時就偏偏從頭到尾使用中遠景鏡頭,那種距離感產生的情緒節制,似乎更有助於觀眾看清一個真實的複雜時代。《羅馬》無疑屬於後者。

導演說:“這是一幅養育我、與我有著親密關係的女性們的肖像畫,它關於愛的識別,穿越了時間、空間與回憶。”這是“我”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不是“我”,而是“養育我、與我有著親密關係的女性”。它敘述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身邊的一個人,它的主角不是作為導演本人原型的、這一家的某個孩子,而是那個負責照顧和伺候他們的女僕。這成了一種天然的間離效應,一種“有距離的第一人稱”。
所以,在這種“有距離的第一人稱”下,克萊奧成為了一個被凝視的“他者”,一個在她的少主人眼裡接受觀看的對象,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體能動性,也使其失去了觀眾的心理代入感——後者也許更為致命。

導演本人當時尚在幼齡,與克萊奧之間既有年歲差異又有性別差異更有身份差異,這使得他對很多事情的認知與判斷,都處於且只能處於模糊狀態。他對克萊奧的同情或者好感,也很難說清究竟來自於發自肺腑的體認,還是一種戀母情結的代償,又或者,只是一種教養、禮貌和孩子氣的善良。
他對克萊奧身上傳遞出的那個更大的社會現實,一直帶著一種“有批評、有不滿、但始終無法悖離自身階層經驗”的猶疑,最後,他只能強行去政治化,把一切歸於“愛可以拯救一切”的廉價。說到底,“一個有錢人家的小男孩講述一個底層女僕的情感掙扎”,這種設定,好像天然就存在某種似是而非的讓人生疑。
正因如此,共情性始終沒能完美地建立起來。克萊奧更像一個功能性的聚焦點,在命運的撥弄裡串起了一整個動盪的墨西哥,但她和她的故事,始終鎖死在一個孩子語焉不詳的回溯、和一廂情願的雞湯裡。這阻絕了這個故事成為一個史詩的可能。
它只是一場動人的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