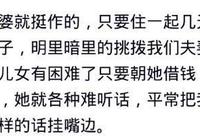救還是不救:那個害死母親的女人,她白血病女兒跟我配型成功了

1
劉一真憂心忡忡地回頭看著摩拖車後座的母親,努力讓車停穩後保持平衡,符萍試著踮平一隻腳落地,扶住劉一真的雙肩,再邁動另一條腿,常人也就三五秒鐘功夫的事情,她磨磨嘰嘰用了兩分鐘。
“媽,你轉轉就回去,回頭下班我路過超市順帶食物,咱倆又吃不了多少。”劉一真不放心讓年邁的母親一個人去市場。
“不用你管,你好好上班去吧,我來散個步。”符萍前後拉了下衣襟,朝女兒擺擺手,示意她快騎車。
距離上班時間不早了,劉一真順著車流駛向大路。
早高峰的紅綠燈不在一個調,綠燈三十秒後,前面一個大貨車堵住,又要等待六十秒紅燈,劉一真低頭看了下腳踏板,發現母親買菜的簡易袋和小布錢包忘了拿。
她側身往路邊上的小商鋪門口停下車,抓起袋子往回跑。母親不習慣帶手機,只能碰碰運氣看能不能尋見她。
符萍高大虛胖,膝蓋骨頭積液變形,兩腿挨著摩擦,走路呈內八字。她來菜場不光是買菜,也算打發時間,偌大的城裡沒有親戚可走動,她一個外地女人,鄰里關係淡漠,講話也有隔閡,只有菜場裡那三塊五塊的吆喝聲她覺得親切。
這是女兒接她進城的第二年,隔三五個月她就要被女兒哄架著去醫院檢查,開的大包小包藥,各種營養品,一換季就幫著買新衣,女兒很孝順,加班加點掙的工資恨不得全花她身上,馬上三十了還沒找到男朋友,也是她的一塊心病。
她最生氣的是女兒揹著她按揭買的房子,說是給她進城養老,和她年輕時一樣好強,她想著休養一段時間就回鄉下了,一個人隨意點,也好比給女兒添累贅強。
市場裡有一塊地方是不用租攤位的,都是周邊農民賣的菜,放一個蛇皮袋鋪開,依次擺好菜類,品相不好但是新鮮,符萍一星期去那轉個一兩回。
清晨下了些細雨,剛把地面打溼,微微有點打滑,符萍站在入口處眺望,貨比三家再決定買哪家的。
菜農並沒有整齊排成一列一列的,來得遲的見縫插針亂擺亂放,中間的過道又擠又窄,兩人並排不一定通得過。
這個季節的油菜綠得掐出水來,每個地攤前擺得滿滿當當,符萍邁開老寒腿跨過去,想問中間那堆紅櫻蘿蔔的價格,發現被人拽住了。
“你咋回事?把我的蔥踩住了!”一位農村扮相大約四十左右的女人揪住符萍的胳膊,大聲質問。
“你老是眼神不好還是腳不好使,你看看那麼生嫩的一把蔥被你踩斷了尾巴,爛趴趴的賣給誰?”
“請你放手。”符萍操著生疏外地口音,很窘迫去掰女人的手。
女人另一手從地上撈起那把蔥,像是有理有據地高舉起,拿給旁邊人看,“你一個外地老太別說我欺負你,你讓大夥瞧瞧這蔥尾是不是斷了?”
符萍多少年沒經歷過和別人吵架的局面,右臉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半生不熟的話像是卡在喉嚨裡吐不出來。
“不為難你,掏三塊錢把蔥買了,你踩壞的你承受。”
“我不買!你放……放手。”符萍牙齒跟著抖動,連一句正常的話說不明瞭。
周圍的菜販,男女老少饒有興趣地看著這一場糾紛,買菜的停下腳步急於看事態的發展。
符萍在女人手上揪了一把,女人“哎喲”放開手,另一隻手撕住了她的外套口袋。
“老太太,把你功夫都使出來,我好歹比你年輕個十幾二十歲,今天你不買下那把蔥你休想走。”女人很瘦黃的臉上顴骨突出,雀斑在兩片嘴脣的上下張合之間跟著跳動。
劉一真沿著前排的商鋪快速找了一圈,打算返回騎車上班,發現十來米外有個背影像母親,穿著暗紅色的毛暱外套,她把眼鏡往上推推,仔細辯認。沒錯,那衣服是她上星期才買的。
在隔著幾步距離外,她高喊了聲“媽”,準備把袋子遞過去。
符萍半彎腰用兩手去抓開女人的手,外套口袋扯得變了形,女人還是沒有放手。
“媽,你們……你們幹啥呢?”劉一真跳進菜攤後,不理解地看著這一幕。
“這下好了,你是她女兒是吧,快掏錢。”女人仰了下脖子,又枯又黃的髮梢垂在耳下,拿起地上那把蔥推到劉一真面前,“三塊錢,算我倒黴。”
“你把我媽放開!”劉一真不知哪來的勇氣呵斥一句,旁邊三三兩兩的議論聲讓她明白了爭執的大概。
“她都快七十歲了,你和她計較?你沒有老的時候?不就兩棵蔥嗎,至於這樣?”劉一真的話語很重,但女人似乎鐵了心不給錢不撒手。
劉一真看著母親向她投來無助的眼神,像是默認了是自己的錯,讓女兒難堪了。
“你再不放手,我就報警了。”劉一真作勢要去拿手機,她覺得這個無賴的女人肯定不是第一回這麼潑婦了,不能便宜她。
女人“哈哈”大笑了兩聲道:“閻王爺我也不怕,怕警察?你趕緊的打電話!”她在地上啐了一口痰,面無懼色地靠近劉一真。
“姑娘你是文化人,別和她鬥嘴,你媽站那麼久可不好。”旁觀者一個大姐善意提醒。
“你高尚,你幫她把錢付了!”女人回了旁邊一句,再沒人勸架了。
女人推了劉一真一把,像是示威,“你快點掏錢,別影響我做生意,現在三塊錢不給,等會給三十我不一定答應!”
只好拉開鏈包,正要往外掏錢,符萍冷不防朝女人頭髮上抓了一把,“莫給錢,不……不準……給。”
女人被抓痛了,把符萍揪到地上,抄起地上的馬紮沒抬頭就往對方打,劉一真拉過母親,馬紮剛好打在她手臂。
符萍看到女兒捱打,在地上掙扎著跟女人扯在一起,泥水和著爛菜葉糊了符萍一身,劉一真攔腰去抱母親,發現她的小體格根本抱不起超重的符萍,她就地坐在母親前面,雙手擋住背後的母親。
女人在地上打了個滾,沒來得及撫弄一下亂糟糟的頭髮,又奔向劉一真。
事態越來越嚴重,圍觀者越來越多,劉一真後悔剛才的言多必失,和垃圾人哪有道理可講,應該默默丟點錢打發這種小人,拉住媽媽離開才是良策。
地上的溼潤很快浸溼了褲子,符萍的呼吸有點急促,就像剛從一樓一口氣走到她們居住的六樓。這種衰老速度讓劉一真時刻保持警惕心,母親的體檢結果,除了一系列慢性疾病,還有隨時要命的冠心病,醫生說過稍微有一口氣急得沒提上來人就去了是常事。
市場管理員來了兩個,有一個徑直走到女人面前,“唐金花,你能不能消停兩天,淨沒事找事,你是不是不想在這擺攤了!”
“你們這些沒良心的,欺負我一個寡女子,這些菜都是我一個坑一擔水澆大的,我賣我的菜我犯王法了?欺負我沒男人,你們也有倒黴的時候啊。”她哭喚得極其有節奏,抑揚頓挫得像是在唱大戲。
符萍碰了下劉一真,低聲說了句,“給她錢,我們走。”
劉一真不解地看著母親,轉念又明白了意思,母親最受不起的是看人哭慘。
工作人員扶起符萍,“盡是些雞毛蒜皮,你們各讓一步不就沒事了。”
看著兩個人泥汙水漿的一身,劉一真掏出五塊錢沒有好氣地說:“拿去吧,當是打發叫花子,你那臭蔥你自己留著吃飽。”不知道是不是憤怒佔了上風,她竟口不擇言說了這句話。
女人毫不客氣接過錢:“想欺負我,沒門。”她還在罵咧著。
劉一真扒開人群幾步追上蹣跚的母親,符萍看她手上空空,馬上返回去拿蔥。
“付了錢的,拿回家!”
看著母親從那女人面前拿起那把徹底揉爛的蔥,劉一真壓制不住心裡的責備,說:“媽,你盡給我添麻煩,我還要趕去換衣服,今天鐵定遲到了,讓你在家哪兒也別去你不聽,能不能先消停會。”
“老了,人沒丁點用了,留在世上有個什麼用處,真的老了。” 符萍喃喃自語。上樓的時候被劉一真扶住,氣喘吁吁,不知是腿疼還是腰疼,幾乎直不起身子來。
“你先回,別管我。”看著女兒著急地盯著看時間,她催促道。
“媽,那我先上去了,你慢慢走。”劉一真三步並作兩步上樓,兩分鐘後換好乾淨的衣服,在四樓平臺處與符萍會合。
“媽,冰櫃裡還有鴨蛋,你中午先湊合著,晚上我買菜回來,你別再出門了,樓梯高難爬,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就行。”劉一真的電話響了,她邊跑邊接,“剛才堵路上了,我馬上就到,對不起,對不起……。”
符萍看著女兒風一般的速度到了底樓,在樓梯邊找了塊乾淨的地方坐下,得歇一會再爬,已經筋疲力盡了。
“媽,媽,你記得把溼衣服換了,放盆裡泡著,我晚上回來刷。”劉一真好像想到了什麼,本能地跑回去,在樓下大喊。
“哎,知道了。”符萍半撐住身子,聽到骨頭髮出清脆的咔吡聲,直到看不見女兒的身影,她才慢揉著膝蓋坐地休息。
女兒原本是個慢性子,她來了之後,變得風風火火的,像個陀螺轉得飛快。要怪就怪孩她爸死得早,沒多生個孩子給女兒作伴,現在自己身體不爭氣,總是幫倒忙。
終於進了家門,符萍坐回窗前的躺椅上,閉目搖晃了片刻。她從冰箱裡拿出兩枚蛋放在碗裡洗淨,然後轉身找來乾淨的衣物去了浴室。
2
一上午對於劉一真來說過得飛快,大半時間在聯繫客戶,馬上到月底了銷量又是傷腦筋的難題,來不及看時間就到了飯點。
劉一真打算先叫個外賣,再打個電話給母親,看她吃了沒有。
同事小敏泡著一盒方便火鍋,對著手機屏幕左看右看,“哎,滿臉痘痘,都是這些油脂惹的禍,我迫不及待想過年了。”
劉一真很好奇:“為什麼?這跟過年有關係嗎?”
“你天天吃媽媽做的美味是體會不到我們這等人對食物絕望的心情。”小敏探過身來,“我當然是想回去吃家鄉菜,說說看,你媽每天給你整啥好吃的了?”
“沒呢,就那老三樣,清淡無辣,一葷一素一湯,我媽節儉了大半輩子,捨不得大吃大喝,她總說‘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一世窮’,她這話夠矛盾吧。”
“那隻要她高興,你就順著她的意,我媽就是一天啥也不幹坐在我面前,我就知足歡喜了。”
劉一真默認地點點頭。
手機鈴聲響起,是個陌生號碼,應該是外賣到了。
“喂--你是601號房主劉一真嗎?”急促的男聲。
“嗯,對的⋯。”劉一真還沒來得及問什麼事。
對方打斷她說:“趕緊的,你家著火了,房裡飄出濃煙,物業已經報了火警。”
“我媽,我媽在房裡,你們快救她出來。”劉一真哭喊著,從辦公室衝出來。
母親單獨操作煤氣廚電用品是沒問題的,怎麼會引發大火?一種不詳的預感衝斥著劉一真混亂的腦子,她催促的哥開快些再開快些。
離門口還有一條街,就聽到消防車的警笛尖銳地長鳴。
3
劉一真跑進小區,花園過道圍著許多人,火撲滅得差不多,只有一縷縷微細的煙塵從六樓鑽出,廚房外牆薰得黑漆,一群帶著工具的消防員進進出出,她轉了兩圈沒看到母親。
“媽,媽⋯媽⋯。”劉一真拉開嗓子沖人群大喊。
圍觀者面面相覷。
“大哥,你看到我媽在房裡嗎?”劉一真拉住一個消防員急切地問。
“上面破拆的隊員還沒下來。”
“我第一個發現的,我正在廚房剝蒜,看到有煙從窗臺冒上來,我叫樓上的人家全跑下來,還去你家敲了門沒動靜,你媽肯定溜街去了。”樓上住戶肖阿姨說。
心急如焚往樓裡衝,她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母親肯定不在家,不在家。
一口氣衝到五樓,就聽到有人大叫,“快,快讓開⋯準備急救!”
心裡的弦像是繃到了極致,剩下的十幾步樓梯,劉一真的腳步似鉛沉重。
母親被平放在過道中央,像是剛從水裡撈出來的,頭髮溼答答,臉上幹著皮的皺像溝壑,毛線衣被水浸得有個分水嶺,任憑消防員爭分奪秒做人工呼吸、心肺復甦,她一動不動。
劉一真咬著右手,麻木了幾秒,她突然躥到母親面前,嚎啕大哭,“媽,媽⋯你快醒過來一一媽,我是一真,我在呢,你別嚇我啊,我好怕⋯。”
又來了幾個醫護人員,劉一真被扶在一旁,各種儀器連接,心肺復甦沒有停。
大約半小時後,醫務人員搖搖頭,表示很是遺憾,收拾醫療器械下去了。
“我們拆門進入發現廚房火勢是由蒸鍋引起的,食物燒乾了,火把燃油機點燃了,吊頂全是可燃材料,在洗浴間發現你媽媽半俯在桶沿邊上,其餘的還需警方來定論。”
人員陸續撤離,劉一真木然跪在地上把母親半扶住,用溼紙巾輕輕擦淨母親的臉,把她的齊耳短髮梳了又梳,像是小時候母親哄她睡覺時,她輕打著拍子悄悄唱:“天黑黑,被蚊咬,要睡覺,長高高⋯⋯。”
老家能通知的親人沒有三兩戶,早年劉一真的父親在工地出了事故,母親在青黃不接時找人借錢,親人間的躲蔽疏離讓人寒心,日子再苦再累,母親也是咬牙堅持,不再伸手求人。
那個遠遠的山嶺,記錄了母親一輩子的辛痠痛楚,劉一真不想讓她再回去,孤苦伶仃長埋在冰冷的地下。她要守著母親,再也不分開。
她從來都認為把母親接來是享清福,卻害她丟了命。
天擦黑的時候,劉一真出了一趟門,哽咽著在照相館裡挑出母親剛下火車時在長廊花園裡照的相片,周圍花朵綻豔,樸實的母親站在金色的陽光裡慈祥溫暖。
“要把背景換了嗎?”沖洗師傅小心問道。
“不用,她還沒走遠,還會回來看我的,我還要帶她去看風景。”
劉一真沒有方向,一直往前走,手裡端著剛洗好的黑白照,她把照片那面緊緊護在單薄的懷裡,她想把自己所有的餘溫都給母親。
一輛出租車急剎在面前,劉一真呆若木雞穿越馬路,司機探出頭大罵:“想死去跳河,別來害人!”
她立在原地細細擦掉相框邊的水珠,用衣袖在母親的臉上拭了又拭。
殯儀館裡其他亡者的靈堂滿堂喧譁,人頭攢動,劉一真靜靜地跪著,有人員過來確認火化時間,她點點頭。還有人來銷售墓地,她便搖搖頭。好像她被一個玻璃鐘罩住了,只有心臟還有滴答滴答聲。
她站在火化爐後面看著升騰的青煙,如果允許她想找一個密閉的口袋,以前聽人說那團煙就是亡靈的靈魂,她不想讓母親四散飄零在空中,直至湮滅。
她摟緊骨灰盒,在床上縮成一團,做了個長長的夢:母親揹著咿呀學語的她越走越快,她高過母親,揹帶斷裂,母親背駝了,形象越來越小,她急得四處尋覓,只看見一團團白霧,寂靜地飄渺著⋯
4
躺屍一般地過日子,終於有一天被窗外穿透的陽光抽到臉上徹底清醒了,劉一真想起了報仇。
她去理髮店把留了多年的頭髮剪短,讓長劉海遮住大半雙眼睛,瘦得如同紙人。然後在網上買了兩把水果刀,幾卷繩子,她覺得唐金花的命必須由她解決。
母親的死,她負有最直接的關係!如果不是把衣服弄髒,母親不會蹲地去洗,她站起時可能用力過猛栽倒下來,那隻大水桶是因為水籠頭扭不緊,日夜滴水母親堅持買來積水所用。當時灶上的鍋裡應該煮著用來當中飯的鴨蛋⋯
誰也阻止不了她殺仇人的心,她甚至想好看著唐金花在她面前慢慢掙扎一點點消失,她再去警局自首,和母親黃泉下團圓。
她摘下眼鏡,帶了足夠多的錢去了菜市場。這些錢足夠買仇人一擔蔬菜送貨上門,在家裡把人殺了。
找了幾天,沒發現唐金花,劉一真騎上車輾轉幾個本地菜市場,唐金花像是算計到自己的劫數來臨躲了避風頭一般銷聲匿跡。
“姑娘,你天天在這轉,是不是找人呵?”一個老奶奶關切地問,旁邊的輪椅上坐個呆滯的老爺子。
“我⋯以前這兒有個女人在這賣菜的,這麼高。”劉一真比劃著,“你知道她住哪?為什麼最近沒見她人?”
老太太努起沒牙的嘴脣,牙床塌陷,臉像一張幹樹皮。
“有沒有名字嘛,這邊賣菜的人可多了。”
“唐金花!”劉一真蹦出的字彷彿像一把刀能揮出寒光來。
“是不是⋯那個怪婆娘啊,呃,聽說她家出事了,是有好久沒來賣菜了。”
老太在圍裙上擦淨手,抓起一把板栗:“這是我昨兒在樹上敲了半下午,粉甜味兒,不要錢給你嘗,看你挺瘦的得多吃點。”
“不要⋯不要。”劉一真不知所措,她放下十塊錢想走,老太滿是繭心粗糙的手觸到了她的皮膚,這真的像母親那操勞的手。她久久地握住老人的手不放。
“你以為我沒錢用啊,我兒孫待我可好了,我帶老伴出來賣點家裡吃不完的,浪費也可惜。半賣半送吧,回去的道上再把錢捐廟裡,我老伴死兩回了,讓我喊回來的,為啥?因為我積福積德,閻王爺不敢收他。”
“人吶,活著不能光等死,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劉一真捧著那窩滾燙的栗子,上面蓋著的十塊錢像在扇她的臉。
生活迴歸尋常,上下班的劉一真每天和燭臺上的母親說說話,把採來的鮮花插下,拂開窗簾通風換氣,日子又有了點生機。
工會找志願者心理師來幫她打開心扉,居委會的大媽大爺輪流上門給予幫助,同事們積極邀約她參加各種活動,她漸漸感受到了社會的愛,三個月後她加入了志願者協會。
水果刀和繩子被她某天打掃衛生時有意無意請進了垃圾桶。
5
充實的工作和豐富的志願者服務活動讓劉一真找到了人生的樂趣。有一次在獻血時,護士無意跟她說了句‘你這麼有愛心可以加入中華骨髓庫,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群’,她沒思索就同意了,抽了一管子血樣,填了幾張表格。
有異性展開追求,同是志願者的阿偉最為熱烈,被劉一真拒絕了,她要為母親守孝三年,之後再解決個人問題,如果無緣就一個人孤獨終老。
週末的一個電話,連劉一真都沒想到她還會再遇見唐金花。
“您好,您的造血幹細胞已成功配型到一位白血病患者,是否同意捐獻,我們尊重您個人的意願。”
打開郵件裡面有個短視頻,女孩奄奄一息躺在病床,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掉光了頭髮,口罩上方的眼圈黯淡無光。一箇中年女人應該是孩子的媽媽跪在媒體面前大呼“救救我的女兒吧,她還很年輕,救救我們⋯”視頻給了婦女一個近距離的特寫,劉一真突然憶起這張臉怎麼這麼熟悉?
反覆確認,真的是她!
劉一真嘆笑兩聲,這算是報應嗎?為什麼會讓她的孩子承受她的罪惡,如果自己不獻出骨髓,唐金花的餘生應該如她剛和母親分離時過得暗無天日吧,這些是她應該承受的!
“謝謝,最近我頻繁獻血,身體還未完全康復,這一次不予捐獻骨髓。”劉一真回覆。接下來的幾天,假裝如釋重負,卻又不自主地在網上搜羅孩子的信息,沒有配對手術的記錄傳來。
似睡非睡的劉一真整夜翻來覆去,她想如果夢見了母親,想聽聽母親的做法。可是,晨光微露時,除了頭痛得厲害什麼也沒夢到。
燭臺上的鮮花變成了乾花,劉一真找來一個盒子晾乾貯存,她不會讓它們變成垃圾,她要妥善地處理任何一樣帶給她和母親慰藉的東西。
“你知道最近本地新聞上那個患病的女孩嗎?據志願群裡說庫裡有兩個是完全符合標準的,但是他們以這個那個理由拒絕了,現在等社會捐款到位,孩子媽媽抽骨髓只有半匹配,康復機率只有一小半⋯。”阿偉坐在劉一真旁邊,看著手機接著說,“部分志願者的服務意識有待提高,根本不會傷身體,如果我能配上型,我絕對會去捐獻。”
“難道你認為那些不主動捐獻的就不是好志願者?你不是當事人你憑啥說這個,你以為這個世界上都是好人?壞人會寫在臉上?她求助代表她是弱者?幼稚可笑!”劉一真抓起外套就走,阿偉一臉茫然,回想剛才哪句話說錯了。
醫院肅靜的長廊,悲涼的白色,唐金花在病床邊半蹲著給女兒喂水,她眼裡昔日的凶芒不在,只有一個母親對女兒的溫情和憫惜。
劉一真推門而入,徑直走到唐金花面前,唐金花仰起頭,說著:“謝謝你們的關心,孩子會好的。”
“請您看清楚我是誰!”劉一真咬住嘴脣,“四個月前,因為我媽踩了你一把蔥,你揪住她不放摔了一身泥,回去洗衣的中午倒在桶裡去世了!她去世了!”
唐金花手裡的杯子掉在地上粉碎,恐慌不已。
“我就是骨髓庫裡跟你女兒配對成功的人,你肯定想不到吧!”劉一真凜冽地直視她,“你覺得我該不該救仇人的女兒?”
唐金花放聲嚎哭:“為什麼老天不懲罰我啊,為什麼病的不是我?我也只是想生存,把自己扮成凶惡相,孤孩寡女才不讓人欺負⋯⋯。”
“夠了!你作的惡,老天都看著,收你也是時間問題。”
6
劉一真心平氣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阿偉,阿偉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我想好了,這兩天就去檢查身體,瞭解捐獻的全部流程,電話已經打給骨髓庫那邊,不會有變了。”
阿偉問:“你真的想清楚了?阿姨在天之靈會不會原諒她?”
劉一真灑脫一笑:“人吶,活著不能光等死,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等去了黃泉,再跟她老人家解釋。”
燭臺像是在無風裡起了點波瀾,燭火更明亮。阿偉緊緊地擁抱住劉一真。
居委會大媽敲開門時,劉一真的笑容凝固了,身後的唐金花正一步一跪一磕首拜倒在符萍的照片前。
“大娘,我害了你,你養了個好女兒,是我對不住你,等我女兒長大成人,我就找你去贖罪……。”
劉一真穿著病號服,守護在手術室外的阿偉向她伸出了大拇指,她做出一個必勝的手勢,平靜且堅定地躺上手術檯,她的耳邊響起刻在心底的承諾:
我志願加入中國志願者協會,奉行“奉獻,友愛,互助,進步”,願意用生命影響生命⋯⋯(作品名:《當仇恨來臨》,作者:木子蘭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