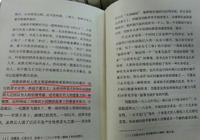“我最初知道《三體》是我學生推薦的,我看了覺得特別奇怪。我必須說他的文字是不夠好的,但是你又覺得他處理人類文明的手法,諸如“三體人要來”的情節,完全不是王安憶、莫言、蘇童或者閻連科可以處理的。在那個意義上,他讓我吃了一驚。”日前,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來到北京領取了首屆“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人物盛典”致敬人物獎項。而在頒獎典禮第二天與人大作家班的學生們的討論會上,他如此評價劉慈欣的《三體》。
王德威進而說,在這個意義上,他花了很大力氣推薦劉慈欣的作品,還曾經在六年前的一次演講中,將劉慈欣與魯迅進行某種比較,他認為,科幻作為一個文類的存在,文學的專業讀者或觀察者必須去正視這個現象。

王德威被認為是繼夏志清、李歐梵之後的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第三代領軍人物,他的筆端遊走於中國文學與歷史之間,從“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斷到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探索,著作頗豐。在致敬典禮的第二天,王德威與人民大學創意寫作班的作家學員們進行了一場對話,圍繞著文學的中心緩緩展開——從臺灣大陸女作家的對比,到中國美國的非虛構文學市場,從王德威的比較文學觀,到中國科幻小說的爆發與影響。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對談實錄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話題一:大陸與臺灣的女性寫作
對語言的自覺磨鍊,是朱天文一輩兩岸女性作家最大的不一樣
孫頻:臺灣女作家像施叔青、李昂、黃碧雲、朱天文、朱天心等等,她們和大陸女作家之間的根本區別在哪裡?
王德威:黃碧雲是香港的女作家,主要作品是在臺灣出版的。我閱讀大陸女作家比較早,我讀的她們的作品都是80年代以前出版的,像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很遙遠的感覺,當然可能你們現在還在讀。另外,像後來去了美國的作家張辛欣,再早的話就是像楊沫、茹志娟等等更前面的一群作家。80年代以前我看到的這些女作家,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性別意識。
我們在海外特別強調性別,這個性別包含社會的、倫理的、情慾的等等方面。那個時候,儘管你能感覺到這些作家在努力嘗試,但不會覺得他們有這麼強的慾望,這麼大膽的慾望,去衝破當時的網絡。
上世紀80年代末期,王安憶寫了“三戀”(指中篇小說《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在中國大陸引起了一些轟動,可是從臺灣讀者的角度看,早在60年代、70年代,施叔青在她年紀很輕的時候已經寫過這些了,儘管場域不太一樣。你會敬重這一時期大陸作家的努力,但如果放在一個女性的立場,你會發現,也許有很多的區塊還沒有仔細發掘。
到了90年代,陳染的作品讓我覺得很有一些和國外相互照應的觀點。後來有一些女作家,像池莉、方方等,她們不能被刻意歸類為女性或者女性某一類的作家。

在這個意義上,再看臺灣的這群作者,其實很有意思。比如朱天文或者朱天心,她們沒有刻意強調作為女作家的立場。當然,由於她們和胡蘭成、三三集刊等之間特殊關係,以至於發展出了很獨特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可以稱作“胡腔胡調”或“張腔張調”,是一種很特殊的表現方式,蔚為風潮。相對於朱氏姐妹來說,施氏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李昂)有臺灣在地的背景,你剛才問到的這幾位女作家裡,早期最強烈地顯示出所謂“女性自覺寫作意識”的,就是李昂。在1968年,她只有17歲,寫了一篇小說叫《花季》,寫一個高中女生上課無聊,跑出去坐在一個老頭的自行車後面,這個老頭看起來是一個園丁,把她載到一個栽滿聖誕樹的花園裡。就是這麼一個莫名其妙地漫遊故事,可意象裡包含著性的隱喻和情的隱喻,尤其是一種青春躁動的感覺。
在這個方面,大陸的作家要到90年代才開始自覺發展。有時候,這個自覺和不自覺不見得有很強的區隔,它就自然而然發生了。在這個意義上,那一輩的臺灣女作家(也包括黃碧雲)在創作上有對語言的敏銳度,這點是重要的。除了自己的性別意識,除了生命裡各種面向的出自女性自覺的探討,我在閱讀時發現,對語言的自覺磨鍊可能是她們那一輩女作家中最大的不一樣。
陳染、林白等作家90年代的作品,你會覺得寫得很有意思、很有趣,或者很能夠觸及到當代共通的女性關懷,但在語言的使用上,可能仍需再進一步自覺地琢磨。這不是是否寫得很美的問題,而是說要有一個特殊的風格。
孫頻:我覺得臺灣女作家比大陸女作家似乎早走了十幾年。
王德威:至於早走還是晚走,當然如果純粹從語言的涉獵、從特定的女性意識的表達來看,的確臺灣作家是自覺的,早走了十幾年、二十年的樣子。像中國大陸作家在80年代的作品——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諶容的《人到中年》等——還在發掘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生育與否、職業發展等等問題,這些東西郭良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寫過了。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郭良蕙這個作家。她生在中國大陸,後來到臺灣,1960年代初期寫了《心鎖》,寫的是姐夫和小姨子暗戀的故事。臺灣輿論把它誇張成了亂倫作品,當時女作家協會的會長謝冰瑩說,如果這樣的作品流行就會把中國文化給毀了,於是把郭良蕙開除出了作家協會的會籍。那是1960年代。郭良蕙有幾個作品都是寫這類題材的,她不是故意要譁眾取寵,就自然地寫了。她不屈服,後來到了國外。所以,很有趣,我會覺得大陸和臺灣女性作家之間有一個時差的問題。

不過話又說回來,你覺得臺灣作家走得這麼遠、這麼早就進行了女性自覺的發掘等等,反過來我要說,丁玲寫《莎菲女士的日記》可是在1928年,這又是另外一個標杆了。所以,在時間上,先來後到是一回事,在不同的語境裡你做出怎樣的因應,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不存在誰進步和不進步的問題。在臺灣的語境裡,臺灣作家的確非常特殊,尤其是女作家,是一股長期主導臺灣文壇的力量。
話題二:非虛構寫作
所有付諸語言的東西,都有虛構的層面
化城:非虛構的概念在中國十分火爆,感覺什麼都可以往上靠,但是裡面也有很多虛構的成分。怎麼界定非虛構的範圍和邊界?
王德威:我不會那麼擔心界定的問題。非虛構不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還強調新聞求真性。既然稱為“非虛構”的話,隱含的意思是:我可以寫成虛構,我只是不把它寫成虛構,其實是給作者一個空間。非虛構的真與假之間有很多真假難辯的問題,那就是閱讀倫理問題了。
我舉一個前兩年臺灣一個文學獎的例子,也許大家會有興趣。這個獎通常有三個獎項:新詩、小說、散文。當年有一位散文作家以艾滋病人的身份,寫他所經歷的情慾、冒險和醫療的故事,講得非常動人。之後被人揭發,他的散文不完全是真的。
通常我們在講散文時,好像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散文應該更貼近我們真實心意的面向。這個散文作者顯然引用了社會報道和他聽來的東西,他用第一人稱寫出了幾乎像是真實的東西。那麼,他應該得散文大獎的第一名,還是小說大獎的第一名呢?這在臺灣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辯。這和你問的非虛構有些相似。
但誰又規定散文一定是100%真實的呢?從這個觀點來講,所有付諸語言的東西,哪怕是報告文學和自傳,也都有虛構的層面。這是一個倫理的問題,未必是作家創作時第一個應該關心的問題。
話題三:文學傳統
中國做現代文學的同行比較缺乏抒情
侯磊:你對民國時期那些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寫作手法的作家特別關注,比如張愛玲、老舍、沈從文等等。但如果我們現在仍沿著他們的路線創作的話,是否還有意義和空間能夠向前突破?他們的創作總讓人感覺與當下的寫作之間有一定隔閡和矛盾,比如不是特別在意經營故事,而更注重環境的渲染。就像老舍的《月牙兒》,他講了母女兩代人做妓女的故事,他沒有主要寫兩代人做妓女怎麼受人欺負、怎麼慘,他著重渲染氛圍——寫母女在月光下互相一對眼,媽媽也明白女兒沒有辦法也去做這行,抬頭一看天上的月牙兒,這輪月牙兒多麼慘。他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去正經講一個故事,而是去寫其他的東西。面對這種創作,我們該怎麼評價?
王德威:你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我對古典文學傳承的看法,第二個問到老舍這類作家經營的特色。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你不覺得《月牙》寫得很好嗎?
侯磊:很好。
王德威:很好就很好嘛。這個作品很好,這代作家不見得能超越。那個世代的作家寫作就是那個範兒,就像十年前很多人想要做現代張愛玲。有一年臺灣有一個比賽叫“誰最像張愛玲”,這是很可怕的比賽,有很多作家參與,還有男的,每個人都去比較,寫出最張愛玲式的小說,這個也太痛苦了吧。何必要跟張愛玲重複呢?我認為,文學是有無限可能性的文字遊戲,這點不需要擔心。老舍他的獨特性,我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但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也有很多很特別的寫作風格,是老舍那代想不到的。
回到你的第一個問題,你覺得我對傳統有這麼深的傳承嗎?我被陳曉明安上過標籤——“優柔寡斷,充滿了情殤”,我一直認為我健康快樂,他怎麼說我充滿了情殤?我沒有刻意去經營一個所謂的“不論抒情”或者“情殤”,我用兩種不同的語言來寫文學評論,沒有英文世界的同行說王德威你寫得好情殤。
但在中文語境裡,很多年前我開始寫評論文字或做文學研究的時候,我想到了兩個點:
第一,做現代文學,除了五四的傳統之外,我們是不是能夠擴大影響,擴大我們傳承的歷史意識,所以我有意無意在呼應這個比較廣義的文學傳統。
第二,既然是我的母語,我就應該放肆一點,有一點自己的風格。但我膽子特別小,你讓我寫出像魯迅式罵人的文字,我每次都怕得罪人,只好“情殤”起來了。
抒情傳統的確是我自覺地和古典的對話。如果說抒情傳統是傷春悲秋、感時憂國,其實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半而已。在我做抒情傳統文學論述的時候,坦白講有海外的立場。1958年,當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的陳世驤教授在臺灣大學做了關於抒情傳統的演講,從此,他引領了至少三個世代的學者對什麼是抒情傳統的認識和研究的興趣。
這個學術問題恰恰是在中國國境以內,我們做現代文學的同行比較缺乏的一個面向。抒情這個東西不是隻是柔軟的、個人的、小資的、王菲式的抒情。屈原是第一個講抒情傳統的人,他講的是發奮與抒情,有著很強烈的政治承擔和歷史抱負,抒情在這個時候激發了所謂中國第一個自覺詩人或者文人的寫作——《楚辭》。在這個意義上,現在我們在被革命跟啟蒙所主導的語境裡面,來一點抒情不為過。不見得是傷春悲秋的抒情,那個可能把我的志氣看小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再一次迴應:是的,我有意在繼承某些傳統上的話語。我個人在大學讀的是外文系,在國外讀的是比較文學系;在國外的語境裡,我們都在使用西方的話語。從我的立場上,我重新回顧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論述的話語對我的影響,我所謂的傳統,不應該只是民國以前的傳統。
我上學期開了一個課講這個話題。我不只教大家熟悉的魯迅、王國維所代表的文論的傳統,我也教了朱光潛、李長之(他是第一部魯迅評論著作的作者)。我也教了一點李澤厚,甚至教了王元化,這裡有你們不能想象的淵源。你們會覺得,王元化不就是一個剛過世的、我們崇拜的文化人物嗎?我當時的設想是,王元化那些年韜光養晦,他看黑格爾《小邏輯》,同時看《文心雕龍》,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了不可思議的辨證關係,後來享譽的《文心雕龍講疏》是他看了黑格爾所產生的靈感,這是我有興趣的。
一個世紀的中國文論家,他們產生的豐富的文論的面向,不是我們今天講福柯、德里達、巴赫金所能夠涵蓋的。到2017年,在我個人的位置上,我可以向我在美國的同行和學生來說明,這一百年中國的文論有它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在比較文學系的同事也能夠說出魯迅曾經怎麼講、巴赫金怎麼講、阿多諾怎麼講,那個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目前我們是一面倒,運用了很多理論模式。
我承認文學傳統對我來講是重要的,但我仍然覺得這個傳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傳統,它應該繼續延續。
話題四:現實照進文學
文學永遠有公眾層面,創作與現實間有落差
蔣方舟:我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作家作品對於社會的參與度,更確切地說,是對公眾事件參與度的問題。我最喜歡朱天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短篇叫《佛滅》,講的是臺灣公益界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我覺得社會性非常強,取材於現實的勇氣也非常值得敬佩。你怎麼看待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樣的經驗?
王德威:文學作為一種用文字表達意義的有想象力的活動,它永遠有公眾的層面。為什麼?語言本身從來就是一個公眾的、大家互相傳遞的符號,沒有一個人可以喃喃自語的寫作,就算喃喃自語寫作的時候,你其實有一個對象是對自己,那個自己已經變成他者,永遠有一個這樣的面向,才能夠形成一種所謂巴赫金式的、有對話張力的論述和小說。
哪怕是沒有一個真正公眾影響力的作品,在他創作的過程中,那個作家自己也必須自覺地認為,他的作品是在某種對話的層次上進行的。這個公共程度跟社會性,一旦真正放諸實際生活的場域裡面,就會有很多有意思的藝術現象產生。
你講的是作家自覺寫作了一個公共的題材,付諸公共的表達,產生公共的效應,這裡面就有取捨,跟社會直接的互動和取捨的問題。這種寫作有的時候是成功的,有的時候不成功。你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你可能沒有看到有的作家寫了半天,號召了半天,還是不成。作家如果是太想用第三個定義下的公共去寫作,恐怕失望是比較多的,你乾脆做記者算了,做電視臺的報道算了。
我覺得,創作的公共性不應該和你對現實生活公共性所的期望劃等號,否則那個創作一定有期望和實際的落差。這個意義上,公共性的確是很難想象的。梁鴻的《中國在樑莊》一出來就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我想她當時雖有公共心的抱負,但未必能預料到反響之大。退一步來講,社會性和公共性是重要的,但是我不會強求作家在寫作時,會預期作品有一個多麼了不得的社會反響,一定要為什麼而寫。
話題五:科幻復興:
中國這十年科幻作品文學品質不夠,但想象力驚人
沈念:這幾年中國科幻作品頻繁走出國門,你覺得這種興盛對社會有什麼意味?或者放大一點兒說,在科幻所屬的類型文學中,作家能夠學習一些什麼東西?
王德威:科幻是晚清小說文類非常特殊的一個發展。晚清小說大宗是狹邪小說,還有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科幻是到了1900年之後,有十年之間突然冒出來的文類,一下子引起了讀者很多的關注和作家寫作的熱潮。那時的科幻小說盡管非常有魅力,但是它的文字基本是不夠好的。晚清的科幻十年是異軍突起的現象,在我的書裡專門有一個章節討論了很多科幻小說和怪異場景,對於未來中國的想象不論是烏托邦還是惡託邦,都讓我覺得非常特別。

現在21世紀又一個科幻熱潮出現。科幻小說很奇怪,在過去是兒童文學。2007年左右,我和北師大的吳巖教授,還有韓鬆、飛氘在上海復旦開了一個會,主題是關於新時期的文學現象。韓鬆和飛氘很謙卑,說“我們是兒童文學作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都覺得特別可笑。
我最初知道《三體》是我學生推薦的,我看了覺得特別奇怪。我必須說他的文字是不夠好的,但是你又覺得他處理人類文明的手法,諸如“三體人要來”的情節,完全不是王安憶、莫言、蘇童或者閻連科可以處理的。在那個意義上,他讓我吃了一驚。
即使到今天我都覺得,整個這十年的科幻作品在文學品質上是有限的,創作基本所依賴的是橫空出世的想象力,這個想象力是非常無羈的。科幻的興起和新媒介的興起是有關的,很多時候科幻小說是在網上先發出來的。
我經常把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科幻,和最近十年的科幻做類比。在這個意義上,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推薦了劉慈欣,其實我完全不認得他。2011年我來人大,講了一個題目叫做《從魯迅到劉慈欣》,當時在座的很多學生都不以為然,覺得這王老師的腦袋有問題了。有學生舉手說這樣合適嗎?
劉慈欣當然不是魯迅,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只是一本作品。我要想講的是,劉慈欣給我的教育是,原來文學有很多種,原來我們在學院裡面正規教的文學是這樣的那樣的,但是科幻作為一個文類的存在,讓你作為一個文學的專業讀者或觀察者,必須去正視這個現象。
從那個意義上,我覺得劉慈欣所代表的現象還有他內在的爆發力,他對整個歷史以外的現象的重新思考,間接影響了我們對歷史以內的思考,這是他們一群作家共同的貢獻,不是劉慈欣一個人的貢獻,其中也包括了韓鬆、王晉康等等。
科幻小說讓我感動,因為在現在作家通常的套路、制式、環境和風格里面,科幻小說家是另類的、異軍突起的,我們希望科幻小說能繼續成長。

劉宇昆對《三體》在美國的推廣起了很大作用。他喜歡劉慈欣的作品,翻譯了《三體》——不只是翻譯,而且做了編輯,變成一個特別好看的英文版《三體》,好看到奧巴馬總統將之列入了聖誕節閱讀書目。那已經是美國的劉慈欣了,不是原來的劉慈欣了。
……………………………………
歡迎你來微博找我們,請點這裡。
也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