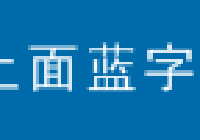怎樣讀·嚴羽及其《滄浪詩話》
嚴羽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家,所著《滄浪詩話》一書,對以後元明清三代的詩歌創作和理論批評的發展都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詩話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中的一種特有形式,從宋代開始大量出現。宋代詩話著作現尚可考者約有百餘種,但其內容十分龐雜。其中大部分是屬於讀詩札記性質,包括詩人軼事、詩壇雜聞、典故出處、字句考證等內容,而象嚴羽的《滄浪詩話》那樣有自己完整理論體系的著作卻是很少的。因此,《滄浪詩話》在宋人詩話中的價值就顯得非常突出。
嚴羽(生卒年不詳),字丹邱,又字儀卿,是福建邵武人,自號滄浪速客,現存有詩歌集《滄浪吟卷》兩卷。嚴羽生當南宋末年,這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動盪不安。嚴羽是一個頗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詩歌中也表達過一些慷慨激憤的情緒,但是,在朝廷腐朽、賣國投降的狀況下,他作為一個普通文人也無力與之鬥爭,只好隱居不仕。他的朋友、詩人戴復古曾在《祝二嚴》一詩中說:“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嚴羽的詩雖然寫得不算好,但是在詩歌藝術的研究上卻凝聚了他的畢生心血。
《滄浪詩話》共分五個部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另附有《答吳景仙書》一文。他關於詩歌的理論集中表現在詩辨與《答吳景仙書》中。下面我們簡要地夼紹一下他詩歌理論體系中的幾個主要觀點。
別材別趣
嚴羽的詩歌理論是針對宋詩中的江西詩派提出來的,自己也以“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詩辨》)自詡。我們知道,詩歌藝術發展到唐代,已經達到了古典詩歌藝術的最高峰。宋詩要有新的創造,必須獨闢蹊徑。在不違背形象思維的前提下,散文化和議論化確使宋詩別具一格,比唐詩又有了新的特色。但是,江西詩派過分強調散文化和議論化,甚至以抽象思維代替形象思維,這就走上違背藝術本身規律的邪道。他們過多地發議論、講道理,排比典故、掉書袋,片面追求文字工巧,這些傾向的惡性發展,對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壞的影響。江西詩派的祖師爺黃庭堅就提出詩歌創作要“以理為主”(《與王觀復書》),“精讀千卷書”(《書舊詩與洪黽父跋其後》)。認為“詞意高深要從學問中來”(《論詩帖》),強諷“無一字無來歷”,“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再答洪駒父書》),提出“奪胎法”和“換骨法”(參看《冷齋夜話》卷一),主張創作要對古人名作“不易其意而造其語”,“窺入其意而形容之”。王若虛《滹南詩話》曾尖銳指出:“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所以,嚴羽把宋詩的主要問題概括為“以文學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是很中肯的。宋詩的這種傾向在蘇軾的創作中已經比較明顯了,不過,蘇軾本人是很懂藝術的形象思維特徵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沒有違背藝術的這一基本規律,因此,散文化和議論化在他創作中構成一種新穎的藝術特色。然而在黃庭堅的創作中,就開始逐漸走向反面。尤其是蘇、黃的一些後學,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傾向,忽略了藝術的形象思維特徵。恰如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所指出的:“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嚴羽《滄浪詩話》的中心就正是為了反對詩歌創作中這種違背形象思維規律的傾向。他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別材”,強調創作詩歌要有特別的才能,並不是讀了許多書,有不少學問,就一定能寫好詩的。“別趣”,強調詩歌應當有一種特別的趣味,具有生動的形象,而決不是隻有一些抽象的道理就能成為詩的。“別材別趣”說,正是為了闡明詩歌的藝術特徵,不把它混同於一般非藝術的文章。這種別材別趣說,曾遭到不少人的攻擊,尤其是一些道學夫子,他們認為詩不能無理,詩人也不能廢學,其實,這都是對嚴羽的誤解和歪曲。嚴羽在緊接上述引文之下,明確地說:“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此兩句《詩人玉屑》引作:“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嚴羽並不否定詩人也要有學問。要多讀書,他認為這對詩歌創作是有好處的,但是書本和學問並不能代替詩歌創作。嚴羽並不是反對詩歌創作中也要有理,而是認為理應當隱藏於藝術形象之中,而不能把說理當作詩。他在《詩評》中曾說:“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嚴羽在這裡所說的詞、理,意興的關係,實質上就是指的語言、思想、形象的關係。意興即是別趣的內容,是指詩歌的審美意象所具有的引起人審美趣味的特徵,用通俗的話說,即是藝術形象的美學特徵。由此可見,嚴羽並沒有否定詩歌中的理,而是主張要象唐朝人那樣,“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嚴羽提出詩歌創作要“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目的是反對宋人以理為詩,以文字為詩,反對用抽象思維方法寫詩。由於他對江西詩派違背豈術規律傾向的深惡痛絕,話是說得過頭了一些。後來,清代的馮班在《嚴氏糾謬》中批評他這兩句話是“似是而非,惑人為最”,這也是有片面性的。馮班說:“詩者,言也。……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又說:詩歌“憑理而發,……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其實,馮班的這種理解,與嚴羽的理解在實質上並無多大差別。嚴羽話說得絕對了一些,但是對藝術特徵的體會,是比馮班要更為深刻的。
妙悟
那麼,怎樣才能掌握別材別趣呢?嚴羽認為要靠妙悟。妙悟本是佛教禪宗的術語,指對佛法的心領神會。禪宗認為至高的佛理是無法言說的,只能靠各人自己去體會,猶如喝水,冷暖自知,一落言筌,只能拘泥於形跡,而不能得其神理了。妙悟,本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宗教哲學思想。嚴羽是藉此來作比喻,認為詩歌藝術的特殊規律(即別材別趣),也是難以具體言說的,只能靠各人自己去妙悟。這樣論詩,也確有禪宗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但是,嚴羽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說明藝術有自己獨特特徵,“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而不是為了去宣傳禪宗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藝術的特殊規律當然不是不能作科學論述的,不過,藝術創作過程中也確有一些微妙之處,常常是難以言喻。對於藝術創作的特殊規律的深入領會和掌握,不僅要從理論上弄懂弄通,而且還要積累豐富的創作經驗和藝術欣賞的能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要有“欣賞音樂的耳朵,感到形式美的眼睛”(《一八四四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因此,嚴羽的妙悟說雖然有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的色彩,但是也有其合理的內核在內。
以禪悟論詩,並不始於嚴羽。在唐代自從禪宗思想廣泛流行之後,禪宗那種“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思想,對文藝創作就有很大影響。司空圖提出“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就很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到北宋就直接出現了以禪悟論詩的說法。蘇軾和黃庭堅都曾有過這樣的論述,但又各異其趣。嚴羽以禪悟論詩是從蘇軾這條線上發展下來的。但他並不是簡單繼承,而是結合當時詩壇的狀況,作了極大發揮的,有自己新的內容。
嚴羽講妙悟的目的,是在反對江西詩派對藝術特殊規律的忽視,他認為詩歌的特點是在“興趣”;因為詩歌以“興趣”為主,所以才需要妙悟。他說:“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那麼,什麼是“興趣”呢?“興趣”,是從我國古代文論中講的“興”發展而來的。對“興”的解釋歷來有兩個不同的角度,一是指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如朱熹在《詩傳綱領》中說的“託物興辭”。二是指藝術寓思想於形象的特徵,如鍾嶸說是“文已盡而意有餘“(《詩品序》),咬然說“興即象下之義”(《詩式》)。嚴羽的“興趣”依據的
是後一種解釋。他說詩歌的興趣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就是對詩歌寓思想於形象的藝術境界的一種形象比喻。只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不能用科學的語言來加以概括,又受到禪宗唯心主義的影響,所以就只能藉助“妙悟”這一概念。因此,我們對他的妙悟說,既要看到其缺陷,也不應全部否定。
嚴羽提出:“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正是為了說明,對於藝術家來說,領會藝術的審美特徵,掌握藝術的特殊規律,乃是最要緊的,否則,他也就成不了一個藝術家。嚴羽還提出悟有“透徹之悟”和“一知半解之悟”,也就是說,對藝術特殊規律的掌握有深淺高下之分,對藝術審美特徵的領會也有浮於表面和深入本質之別。一個藝術家如果只是“一知半解之悟”,而不能達到“透徹之悟”,那也還是不能寫出好作品來的。嚴羽講悟,只是一種比喻,以禪悟比詩悟,並非真是要從詩中悟禪,因此,他在講如何去悟的時候,具體的途徑是“熟參”古人之詩,從古人的好詩中悟入,進而又提出了“第一義之悟”的問題。“第一義之悟”也是佛教術語,指領會佛法的最高境界;對詩歌來說,是比喻要從最能體現藝術特殊規律的詩中去悟入。嚴羽認為,必須從第一義之悟悟入,方能達到透徹之悟;然而從第一義之悟悟入,並不一定都能達到透徹之悟,也可能只是一知半解之悟。只有既從第一義悟入,又達到透徹之悟,才是最高境界。
識
怎樣才能從第一義悟入,並達封透徹之悟呢?嚴羽認為要依靠“識”。《滄浪詩話》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夫學詩者以識為主。”“識”,也是佛教的術語。在詩歌理論中,也不只是嚴羽一個人講“識”。江西詩派也講“識”,那無非是指如何識別“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妙而已。而嚴羽講“識”,則是指的對藝術特殊性的認識,是一種藝術鑑賞的能力。善“識”,然後方有可能從第一義悟入,並進而達到透徹之悟。嚴羽認為“識”有兩個要求:一是“入門須正”,二是“立志須高”。既要走正門大道,又要立較高的標準,從漢魏盛唐詩歌的最高境界中悟入,方不至於會讓下劣詩魔侵入肺腑之間。只要學詩的方向對了,即使“行有末至”,仍“可加工力”;如果方向錯了,那就會“路頭一差,愈騖愈遠”。嚴羽之所以強調以盛唐為法,從藝術成就最高的詩歌中悟入,也還因為“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這是很有道理的。
關於“識”的能力,嚴羽認為主要應通過“熟參”名家之詩來培養。只有“見詩之廣,參詩之熟”,才可能具有“真識”。他說,如果能對自漢魏至宋代的名家詩均“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也就是說,只要對名家之詩作深入的比較、研究、分析,自然就能具備正確分辨好壞的藝術鑑賞能力。經過這樣的“熟參”,如果還不能“識”,“則是野狐外道,矇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嚴羽把“識”最終歸結到要“截然以盛唐為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也是他有見識的一種表現。但是,嚴羽沒有看到詩歌刨作的真正源泉是生活;詩歌藝術的發展,雖然必須學習、研究、繼承前人經驗,然而,最根本的還是要從現實出發。學習、借鑑前人創作,不能代替自己的革新創造,否則,藝術就不能發展。後來,明代前後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走上覆古模擬的死衚衕,使其創作“高處是古人影子”(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正可以說是對嚴羽詩歌理論中這個缺陷的惡性發展。
嚴羽的詩歌理論雖然存在著不少弱點,但他重視詩歌藝術的特殊規律這一點,對於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從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發展上看,應該給以足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