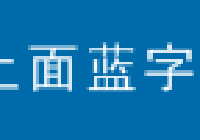“十三經清人註疏”緣起
徐 俊
就對中國古代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言,“十三經”可以說超過任何一部典籍,顧頡剛先生稱之為“吾國文化之核心”,“中國二千餘年來之文化,莫不以此為中心而加以推揚”[1],所以在整理和傳刻方面,歷來倍受重視。尤其是清代經學大盛,註疏之作,遠邁前賢。自章太炎、梁啟超起,即有重訂經疏之議。1933年陶湘等創議匯刻“十三經義疏”,1941年顧頡剛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主持印行“十三經新疏”,但限於條件,擬目既定,未遑措手。中華書局自1920年代《四部備要》遴選清人“十三經”註疏首次整理排印之後,於1960年代提出“清經解輯要”出版計劃,廣納眾議,歷經周折,最終形成了“十三經清人註疏”叢書,於1980年代開始陸續整理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一直受到國家主要領導人和政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資治通鑑》和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4到1956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由顧頡剛、聶崇岐、王崇武等12人組成標點小組,完成了《資治通鑑》的整理。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議[2],後來由毛主席直接部署,經吳晗、范文瀾、金燦然等籌劃安排,於1958年正式啟動,次年第一種《史記》出版。
相對於歷史典籍,被劃屬哲學範疇的經部典籍的整理,受關注和重視的程度明顯不夠,或者說,能否出、如何出,在當時頗成為問題。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華書局改組為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當時,中華書局編輯部分為歷史一組、歷史二組、文學組、哲學組,據陳金生先生回憶,當時哲學組的中心任務是整理出版一套“中國曆代哲學名著基本叢書”,但是具體出版物並不列叢書名,包括後來列入“新編諸子集成”的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吳則虞點校《晏子春秋集釋》,列入“道教典籍選刊”的王明《太平經合校》,以及列入“理學叢書”的《葉適集》、《何心隱集》等,都在這個系列計劃中。另外還與中科院歷史所思想史組合作,編輯出版《中國唯物主義哲學選集》和《中國思想史料叢刊》,著手編輯《王夫之全集》等[3]。哲學組的組長由副總編輯傅彬然兼任,這一時期中華書局經部和子部典籍的規劃出版,大多與他有關。
1957年,中華書局用《四部備要》舊紙型重印了《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全40冊。“十三經”新本的整理工作,隨著《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的制訂和頒發逐漸展開。1960年3月24日,顧頡剛先生給傅彬然信[4]:
彬然先生:
昨接電話,敬悉一切。
二十年前,客居成都,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其時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設立史地教育委員會,邀我參加,囑我定出整理“十三經”工作的計畫,我就寫了《擬印行十三經新疏緣起》及《整理十三經注疏工作計劃書》兩篇寄出。但後來此事交給國立編譯館辦理,我即未與聞。勝利後,編譯館復員回南京,不幸舟覆江中,此項稿件損失甚多。惟焦循《孟子正義》一種交我審查標點,留在我處,幸而獲免。現在把舊作二篇、焦書一部送上,敬祈檢覽。焦書系李炳墋同志所點,他現任合肥安徽師範學院教授,如可出版,請徑與接洽。
敬禮!
顧頡剛上 1960.3.24.
信後附顧先生1941年所寫《擬印行十三經新疏緣起》及《整理十三經注疏工作計劃書》的抄件。傅彬然於次日收到此信,有如下批註:“顧所擬與我們設想基本相同”,“請童老(引者案:即童第德,哲學組編輯)提意見。彬然25/3”。這裡所謂“與我們設想基本相同”,是指“十三經新疏”,“新疏”即清人經解著作。顧頡剛《為編十三經新疏致專家函》說:“遜清一代,經學昌明,學者奮其精思,不辭勞瘁,往往以一人之力綜合前修百世之功,縱有未密,亦已十得七八。爰擬先取此類鉅著,彙刊一編,名之曰‘十三經新疏’”。所列書目,為每經選清人註疏一種,另附錄四種。
1962年初,中華書局編輯部形成了“《清人經解輯要》整理出版計劃(草案)”,並印發徵詢有關方面的意見(62編字第299號):
為了滿足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我局擬對清人經解的主要著作進行整理,現附上計劃和書目一份,希就以下幾點,提示意見:
(1)這一套書只包括清代漢學家著作,宋學家解經著作擬另行整理。這種做法是否合適?您認為書目有哪些需要增刪的?
(2)各書採用什麼版本作底本合適?校勘工作作到什麼程度?
(3)請推薦各書的您認為最合適的整理者。
您還有什麼其他意見,也請一併見示。您的意見盼於三月底以前擲下。不勝感荷。
此致
敬禮!
中華書局編輯部 1962年2月22日
所附“《清人經解輯要》整理出版計劃(草案)”除第五條為選目外,前四條如下:
一、經書是我國的重要古籍。清代漢學家解經,成就超越前世。但清人解經著作的刊本現在大多不易購得,為便利研究工作者參考起見,茲將清人解經的主要成果,編為《清人經解輯要》,整理出版。
二、這裡所謂經書是廣義的,除“十三經”以外,還包括《大戴禮記》、《逸周書》、《國語》和《說文解字》。
三、整理工作的體例將另行擬定。
四、這一套書以叢書形式出版,但暫不列叢書名稱。
中華書局編輯部於3月15日收到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彙總寄回的書面意見,依次為屈守元、魏炯若、雷履平、張白珩、劉念和、徐仁甫、湯炳正、劉君惠八人,均為各自親筆,寫於3月9日。其中屈守元、湯炳正二位先生所提意見最為周密。
屈守元先生提了六條意見:
一、既名《清人經解輯要》,即非“十三經新疏”之類,因而用不著對每一部經書平均照顧,選入一些第二流(如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等)、第三流(如朱彬《禮記訓纂》等)著作。
二、清人經解的權威著作如《經義述聞》、《廣雅疏證》決不能遺漏。
三、易類只印惠、焦之書已足。書類孫疏不如王鳴盛、江聲二家,王氏《參證》更無可取。《逸周書》有朱可以去陳。詩類陳、馬、胡三家同印甚好,王氏《集疏》反不如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精當通用。《禮記》清人所作不能超過孔疏,可以不用朱書勉強備數。春秋類可以增加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說文段注》應附馮桂芬《考正》。
四、皮錫瑞《孝經鄭註疏》誤為《孝經鄭疏補》。
五、是否可以先印正續兩《經解》(用縮印的辦法,如印《冊府元龜》、《宋會要輯稿》那樣),全部供應,也可擇最要者單行。然後組織力量編選《清經解三編》(用影印的辦法,擇原刻本或精刻、精校本縮印,開本大小與兩《經解》一致)。若能如是,對學術界的貢獻,比這個輯印的計劃大得多。
六、如果這一套書要整理的話,請特別注意斷句的工作。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左傳舊註疏證》句讀錯誤的地方太多。
湯炳正先生提了三條意見[5]:
1,在體例方面,如果依照舊例,小學附入經學,則《說文》、《爾雅》之外,應當增加《廣雅疏證》、《方言箋疏》等書,同意劉念和的意見。如果將來還要整理出版清儒有關小學的著述,則這一套書內可以不收《說文》。至於《爾雅》為解經之作,當作別論。
2,選目方面,今古文家兼顧,比較精當。王先謙在《尚書》方面無成就,《尚書孔傳參證》是否可以換為王鳴盛的《尚書後案》為恰當。
3,如果將《說文》收入本編,則在段氏《說文解字注》之後,是否可以援《大戴禮》之例,把鈕樹玉的《說文段注訂》、徐承慶的《
說文段注匡謬》附在後面。
另外幾位先生的意見中,魏炯若推薦羅孔昭,徐仁甫說羅孔昭可以整理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或《大戴禮記補註》、《大戴禮記解詁》;雷履平建議擴大範圍,將《經籍篹詁》、《經義述聞》也收進去,並建議編《皇清經解》正續編的索引;張白珩建議加上徐乾學《讀禮通考》;劉念和說既已選《說文》,《方言疏證》、《方言箋疏》和《廣雅疏證》也應收入;徐仁甫建議不選焦循《易通釋》,增收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王念孫《廣雅疏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劉君惠認為名物考訂也是讀經的重要手段,如程瑤田《通藝錄》一類的書,可以選入一兩部。
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楊向奎先生也對選目提出了增刪意見,並做了如下說明:
陳逢衡《逸周書補註》 作得不好,沒有什麼用處。關於《逸周書》還是孫詒讓的《周書斠補》(有家刻本)好。劉師培的《周書補正》等也有可採。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改字太多,殊嫌武斷。此書可重作。
朱彬《禮記訓纂》 簡陋,沒有什麼用處。《大學》、《中庸》兩篇沿元人陋習缺而不注。《禮記》還是鄭玄注、孔穎達疏好,後人都趕不上它。衛湜《禮記集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也有用處。清末以來有些人想刻十三經新疏,《禮記》最無辦法。為了成龍配套,便看上了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和朱彬的這部書。孫希旦是宋學,朱彬就更走運些。如果為了成龍配套,目前只可印此書(此後也不會有人作《禮記》新疏,低手作不了,高手不肯作。《禮記》內容太亂,事實上也沒法作),否則便不當印(此書流通尚多,有家刻本,清末以來石印本,四部備要本等,好買),不如印衛湜《禮記集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還有些用處(各家佚說多賴此以存)。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 偶有比孔廣森詳細的地方,從大體看印不印沒有多大關係。建議印幾種難覓的《夏小正》,如宋書升《夏小正釋義》(葉景葵有抄本現在上海圖書館)、雷學淇《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有家刻本)等。
秦蕙田《五禮通考》 清代有些作官的人對此書評價極高,幾乎皆備此書,因為禮是國之大事,讀此可以為當時政治服務。今日看來沒有什麼用處,因為考三代的禮有專門的書很多,秦漢以下的禮皆是沿襲虛文,又不必講。建議印王紹蘭的《禮堂集義》(原稿在上海文管會或圖書館,有自序見《許鄭學廬存稿》),這是一部大書,彙集幾百家之說,對研究三禮會有一些用處。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此書無用。建議印王樹柟的《左傳疏》,聞原稿在北京圖書館。
鍾文烝《穀梁補註》 此書不好亦無用。建議印柯劭忞《穀梁傳注》(有北京大學排印本)。
除對上列諸書的意見外,楊先生也建議增補王念孫《廣雅疏證》並附校補札記等。
對照《十三經新疏》和《清人經解輯要》兩份目錄,主要的差異之處有兩項:一是後者取廣義的經書概念,除“十三經”以外,包括了《大戴禮記》、《逸周書》、《國語》和《說文解字》;二是各經沒有嚴格限定入選著作的種數。也因此學者們所提意見,範圍更加擴大。在這份計劃草案發出之前,負責哲學組工作的傅彬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將自己的想法向金燦然作了書面彙報:
燦然同志:
昨天傍晚,收到關於整理印行清人註疏本的各項文件。今天向嚴(健羽)同志問清經過情況後,又重新看了一遍。認為計劃定得太大,還是照您指出的第一點“就顧的方案,吸收童、章的意見”,另擬方案好。這套書的名稱,也待研究,最好還是用上“十三經”字樣,與“二十四史”、“四書五經”等名稱相對。內容仍以原“十三經”為限,《孝經》仍然保留(讓大家見識見識《孝經》也好,我沒有讀過《孝經》,也從沒有翻過《孝經》,到前年拿來翻了一下,才知道是怎麼樣的書)。《爾雅》是字書,與他書比,思想性較少,但既然原來列入了,還是讓它保留。每經以一種為原則,必要時可另加一種,如《孝經》、《爾雅》就不必加了。總數限定在二十種以下,每種書重複不超過一種。硬性規定,比較好辦。照現在的擬目發出去,讓這麼多人提意見,將會搞得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曠日持久,反而妨礙工作。今天先向您提出這個原則,如認為可以考慮,再來定名稱、擬目,定做法,然後去請教別人。如果確定這樣做,就由我來負責,一個星期之內向童、章等商量,提出初稿。匆匆不盡,餘容以後詳陳。此致
敬禮
傅彬然 2,16 下午
此函中兩次提到的“童、章”,是當時哲學組老編輯童第德、章錫琛先生。在原信末行有傅彬然親筆:“原信字跡寫得太草率了,怕看不清,煩季康同志重寫。”另有紙條補充說明如下:
剛才寫奉一信,再補充幾句,關於印行清人經解,我現在的想法,和過去有所不同。原因一則從傳統“十三經”這一名稱著眼;二則新增加《國語》、《逸周書》等,道理並不頂充分,前二者是史書,後者(引者案:指《說文解字》)是字書。再致
燦然同志
傅彬然 二、一五下午 五時半
傅彬然的意見當時應該是沒有被接受,所以才有前面已經述及的印發計劃草案徵求各方意見的事。
《清人經解輯要》的計劃在陸續收到各方面意見之後,還在不斷商討之中。在我們從網絡購回的檔案中,有傅彬然《重印十三經的一些想法》兩紙(另有他手抄的“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清十三經目錄”一紙),其上另有給金燦然的紙條:“關於重印‘十三經’的一些想法,請燦然同志核定。傅彬然4/10。”金燦然批示:“第一件事同意,請即辦。第二件事待第一件有眉目後再辦[6]。金5/10。”[7]
傅彬然《重印十三經的一些想法》共四條:
一、選清人注“十三經”一套,名《清人十三經注疏》,選目擬以尹炎武寫緣起的為主,請童第德、顧頡剛、陳乃乾等同志一商。所以不稱“清經解”,因為這名稱看起來範圍太廣。《皇清經解》、《續經解》不附原經全文,將來可考慮選印。——清經解可印者似不能限每經一種,這一套出版以後,仍然可以續出單種。
二、楊、張擬目第二輯中各書,不必一定稱“經解”;關於解經部分,多收入“經解”;其中多數可作讀書筆記出,陳乃乾同志有此計劃。
三、《清人十三經注疏》的印行方法:選擇善本,斷句印行(經文依黃侃短句)。開本大小、裝訂,仿“二十四史”。這套書的目的,供新專家閱讀,能全用新式標點重排更好。
四、“十三經”白文,作工具書用,照黃侃校本印行,與此配合,另編索引。
原件附抄了尹炎武執筆的《匯刻十三經義疏總目錄及緣起》5頁,末署“民國廿二年十月丹徒尹炎武石公記於舊京後泥窪之繙經室”。匯刻“十三經義疏”由陶湘創意,楊鍾羲、張爾田、傅增湘、陳垣、董康、孟森、丁福保、閔爾昌、高步瀛、胡蘊玉、吳承仕、邵瑞彭、餘嘉錫等二十餘人蔘與商定,《緣起》雲“日夕商榷,書問十返,各屏異執,成茲總目”,共五百卷(附錄在內)。但“雕造須時,糜金十萬(全書都一千二百數十萬字,需款十萬以上),一人一地,必難獨任”,最終未能印成,僅有朱印樣本一冊留世。
從傅彬然所提四條,可知當時有分輯出版,並另印“十三經”白文的計劃(楊、張擬目未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傅彬然在此第一次採用了“清人十三經注疏”的叢書名,後來一直沿用的整理和出版形式也已基本確定,並且得到了金燦然的同意。
事情要再往前回溯一下,中華書局編輯部1962年2月22日具文發出徵求意見的《清人經解輯要》計劃草案,同時也呈報文化部黨組書記、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徵求他的意見。齊燕銘於同年10月1日作了如下批示:
燦然同志:我認為這步工作暫時可以不作。因為:這些書大多數為近刻,易得。經學還沒提到研究日程,如何研究也還值得考慮。其次,如此計劃所列的書,體例不一;如一般涉獵,並不便於初學;如為專門研究,又感不足。如何辦,可以遲一些時候看看學者需要再來考慮。齊燕銘 1/X
齊燕銘是章門弟子吳承仕的學生,於經學當是內行,所以才有這一番關於“初學”與“專門研究”的評估。其實,更要緊的可能還是“經學還沒提到研究日程,如何研究也還值得考慮”這句話。自漢至清,經學在各門學術中都佔據統治的地位,但與當下“古為今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宗旨,卻不甚相符,時機尚不成熟,這也許才是“這步工作暫時可以不作”的真正原因。金燦然看到這個批示,應該不無意外,因為他剛剛在傅彬然《重印十三經的一些想法》上寫了“請即辦”的批示,現在又在齊燕銘的批示後面寫下:“照齊批辦。”這一天是1962年10月5日,“清人十三經注疏”的計劃被叫停。
十年之後,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重新啟動,由顧頡剛總其成。周總理派吳慶彤同志到他家看望,並轉達總理對“二十四史”標點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會議上,總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標點,十三經也要標點。”[8] 又過了十年,1982年,中華書局重新啟動“十三經清人註疏”叢書,在這年5月起草的《十三經清人註疏出版說明》後,附錄了列入叢書的24種書的目錄。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選目綜合了《四部備要》本清人十三經書目和尹炎武等“十三經義疏”、顧頡剛“十三經新疏”的擬目,尤其是承續了在“清經解輯要”擬目及各方意見基礎上傅彬然提出的“清人十三經注疏”方案,可以說“十三經清人註疏”叢書計劃,是中華書局編輯部和過去幾代學人編纂設想的匯結。
2012年4月4日,清明
2012年4月17日晚改
附錄:十三經清人註疏選目對照表(略)
[1] 顧頡剛《擬印行〈十三經新疏〉緣起》,抄本。
[2] 《談印書》,《人民日報》1956年11月25日。
[3] 陳金生《二十八年為書忙——述哲學編輯室的工作歷程》,《回憶中華書局》下冊,85頁。中華書局,1987年。
[4] 此信《顧頡剛書信集》失收,所據為網絡圖片。
[5] 《湯炳正書信集》收錄,8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
[6] 傅彬然所說第二件事為:“又,擬印《二十二子》。一天,與顧頡剛同志閒談,他提出影印浙江書局版《二十二子》,我以為頗可考慮,主要作工具書用。《諸子集成》式的將來還是要作。”
[7] 原件沒有明確的紀年,根據內容推測,應是1962年10月5日。
[8] 《光明日報》1979年3月6日。
四問《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
四問《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
讀書報專訪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
訪談發表於2012年3月“十三經注疏匯校”啟動之際(《中華讀書報》2012/3/28),時隔兩年,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杜澤遜先生主持的“校經處”46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項成果《尚書註疏匯校》完成初稿,3月29日在山東大學舉行了專家審稿會。即日泉城歸來補記。
讀書報:《十三經注疏》是我國古籍中的基本典籍,與“二十四史”構成傳統典籍的骨幹。我們知道,30年前,中華書局出版了“二十四史”點校本,這已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的經典。為什麼“十三經”沒有做同樣的工作?
徐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是過去幾代學人都曾計劃要做的一件事。就古代典籍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言,“十三經”的影響超過任何古代典籍,顧頡剛先生稱“中國二千餘年來之文化莫不以此為中心而加以推揚”,所以在整理傳刻方面,歷來受到大家的重視。
單就現代古籍整理意義上的“十三經”整理而言,我們可以以顧頡剛先生為例來說明。早在1926年顧先生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助教的時候,就提出整理《十三經注疏》,包括校勘、標點、纂輯、索引四個方面,目標是“使學者對於宋以前之經說開卷瞭然”,“基礎既固,自不難於堂構”(顧頡剛1926年5月《整理十三經注疏計劃》)。次年顧先生就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之前,還曾致信胡適,計劃請范文瀾參加標點《十三經注疏》,重校“十三經”正文。1941年,顧先生在成都,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受當時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託,主持《十三經注疏》整理,顧先生提交了《整理十三經注疏工作計劃書》,後因工作轉移,未能完成。在顧先生1950年代日記中,“標點本十三經”、“十三經點校”也多次見於他的學術計劃中。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特別重視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毛主席曾經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強調剔除糟粕,吸收精華和“古為今用”。1954到1956年,在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下,由顧頡剛、聶崇岐、王崇武等12人組成標點小組,完成了《資治通鑑》的整理。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議,並滿懷豪情地說“這是千秋的事業”。“二十四史”點校從1958年啟動,次年第一種《史記》出版。
那麼,在此前後,是否有整理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十三經”的動議呢?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制訂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點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規劃,“十三經”則以清人註疏著作為主。1960年至1962年間,中華書局由傅彬然等牽頭,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執筆)、1940年代顧頡剛等學者關於“十三經”整理的意見,制訂了“十三經注疏”及清人註疏著作的整理方案,並在全國有關高校徵求了意見。但最終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未能開展。
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重新啟動,由顧頡剛總其成。周總理派吳慶彤同志到他家看望,並轉達總理對“二十四史”標點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會議上,總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標點,十三經也要標點。”(《光明日報》1979年3月6日)1979年,中華書局恢復獨立建制後,即著手以“十三經清人註疏”叢刊的形式,對“十三經”重要註疏著作進行系統整理。
讀書報:關於《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一事,山東大學與中華書局是什麼時候開始聯繫的,過程如何?
徐俊:組織整理出版一部比肩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十三經”通行本,是中華書局多年規劃和準備做的一個重大選題。中華書局與山東大學文史哲學科有著悠久的合作歷史,“二十四史”點校本中的“南朝五史”就是山東大學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先生經過十餘年整理完成的。十多年前,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著手“宋本十三經彙編”,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中華書局也是承擔單位。2006年,我們在進行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的同時,也開始著手“十三經注疏”通行本的準備工作,包括體例制訂、文獻準備和學術資源等方面,並與山東大學儒學院密切合作,多次研究磋商,確定了工作方案。項目已經列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制訂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我們認為由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十三經注疏》的匯校、點校,出版一部“十三經”現代通行本,是適逢其時的學術文化盛事。
讀書報:“二十四史”點校本出版時,我們國家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中華書局就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機構,加上由最高領導人發起,因此動員、組織全國學術資源非常便利。現在看來,這樣的條件是無法複製的,這對《十三經注疏》的匯校、點校會有影響嗎?
徐俊:當然,隨著學術環境、出版環境的變化,半個世紀前“二十四史”點校的模式,現在看來已很難複製。但是,今天的條件,也有很多方面遠遠優於當年。比如,國家對文化工程的重視,雖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來推動,但在宏觀規劃、項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期;再比如,學術界幾十年學術積累和專題研究的深入、文獻資料的彙集和利用,也大大超過從前;新科技帶來的便捷,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進程。另外,就本項目而言,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前期準備工作充分紮實,已確定的以“匯校本”為基礎,最終形成“通行本”的工作方案,符合學理,符合古籍整理規範,也滿足了目前學術界、社會文化界的基本需求。中華書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一支優秀的編輯隊伍和豐富的編輯經驗,匯校工作主要由山東大學方面承擔,通行本將在全國範圍內遴選經學專家分別主持,多方通力合作,保證《十三經注疏》匯校本、通行本的順利完成。
讀書報:完成一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點校本,目前的學術積累是否成熟?比如,有沒有一些重大的學術爭論難以形成共識,再比如,在未來可預計的一段時間裡,會不會出現新的學術研究突破,等等?
徐俊:關於《十三經注疏》的學術積累是不是能夠構成當代《十三經注疏》整理,尤其是點校通行本的基礎,我認為大體說來是能夠構成整理通行本的基礎的。“十三經”以及它的註疏在唐宋時期,事實上是科舉考試的標準,在後來歷朝歷代都沒有停止研究,這種研究在清代達到高峰,《皇清經解》正續編、《清經解三編》大體集中了比較重要的成果,近幾十年有新的方法以及發現的新材料,使得經學研究有新的進步,有關的成果也比較豐富,海內外發現的早期的版本比以往更多,使用也更方便,應當說條件已經相對成熟。點校首先是校,校要依賴不同的版本,尤其是早期的版本,這一點條件比前人優越。再就是斷句,全部《十三經注疏》在乾隆年間已經有了比較好的斷句本,當代學者沒有很好利用,近一二十年間,學術界在標點方面也做出了較好的成績,都是可資借鑑的。因此,斷句方面也有了較好的積累。總體上看,需要進一步努力的仍然在校勘方面,條件較好,但是工作量巨大,需要一定的週期,不能搞大躍進,只要方法得當,依靠專家,這項工作是可以順利完成並且達到預期的目標的。當然,“十三經”、“二十四史”都存在懸而未決的問題,先秦兩漢的古書問題非常多,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做點校工作,古籍整理一般採取謹慎的方法,對於有疑問的地方,可以沿用舊說,不勉強做新解,這種妥當的做法是古籍整理界公認的,因此也不會成為當代整理通行本的障礙。至於今後有新的、更好的研究成果,這在所有的古籍整理中都是存在的,那就應當在適當的時機做修訂工作。“二十四史”點校本正在修訂,就是基於這方面的原因。因為“二十四史”點校本問世以後,商榷、訂誤的文章發表的不少,可以參用的文獻資源也發生了巨大的擴容,應當吸收到修訂工作中。總的說來,這項工作並不存在一個終極點,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關於《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
《十三經注疏匯校》
《十三經注疏》傳世版本,大體說來有九個系統:(一)宋刊單疏本,(二)宋刊八行本,(三)宋元刊十行本,(四)明嘉靖李元陽刊本,(五)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刊本,(六)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七)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八)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本,(九)清嘉慶阮元南昌刻本。匯校《十三經注疏》,這九大系統的版本應當通校,所有異文均應忠實地寫入校勘記,形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長編》。《四庫全書薈要》本是不是可以斷定為獨立的版本系統,要通過校勘來確定,所以在實際工作中要對《薈要》本作專門的校勘。其他註疏系統的重要版本,例如《尚書註疏》蒙古刻本,《論語註疏》宋蜀刻本、元元貞平水本,《儀禮註疏》明陳鳳梧刻本、嘉靖應檟刻本、清張敦仁刻本,南宋劉叔剛一經堂刻《毛詩註疏》《春秋左傳註疏》,南宋福建刻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註疏》等,也要列入全面對校的範圍內。
《十三經注疏》最早的版本系統為“單疏”系統,傳世有宋刊本(或傳抄、重刊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穀樑》、《爾雅》等,面貌最古。
另一較早的版本系統為經註疏合刻本,即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八行大字本,傳世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紹興府刊)、《論語》、《孟子》。
第三大系統是十行本,又稱附釋音《十三經注疏》,南宋建刊,元有翻版,明南監據以修版,阮元《十三經注疏》所從出。
十行本之後,有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清嘉慶阮元南昌刻本,都以十行本為祖本。
本來元刊明修十行本,亦即明清各本的祖本,適合作為《匯校》的底本,但就目前情況看,存在以下問題:一、“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經注疏》十行本,一半以上為明正德、嘉靖修版。根據前人的校勘,重修版錯誤校多,並且有闕字。二、其中《儀禮》不是註疏本。因此,無法作為《匯校》的底本。後來的版本,李元陽刻本出於元刊明修十行本,校勘不精,闕字大都未能填補。汲古閣本出於北監本,校勘不精,質量在北監本之下。乾隆武英殿本文字校勘方面勝於北監,其勝處往往與宋本合,大抵參考了何焯校宋本,並且加了句讀,是較為精善的版本,但是為了行文明暢,對疏文引用各書偶有更動,各篇解釋篇名的疏文原在各篇,殿本統一移到各書卷首,疏文開頭“某某至某某”的提示語也被刪去。四庫本又據殿本而再加校勘,均稍失原貌。則可考慮作底本的只有明萬曆北監本和清嘉慶阮元刻本。阮元刻本附校勘記,比較通行易得,如果選為底本,其校勘記是否保留,頗難定奪。如不予保留,則所謂阮本實際不全,如予保留,則校勘記外再加匯校,不無疊床架屋之病。基於以上考慮,選用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作為底本,似較妥當。北京國子監本源於南監重修十行本,根據前人的研究結果,當時曾據宋版校正,改正錯字,填補闕文,屬於較為完善的官版。明崇禎年間曾對初版進行修補,修補版錯誤較多,阮元校勘記所利用的明北監本為修補版,所以阮元對北監本評價很低。這是一種誤解。
《十三經注疏匯校》的具體工作步驟是:以北監本與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四庫》本、阮元本分頭對校,形成八份校勘記。再將八份校勘記合成一份校勘記,也就是所謂的“匯校”。
歷史上形成的《十三經注疏》的校勘成果,如武英殿本《考證》、《四庫全書考證》、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補遺》、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劉承幹刻單疏本校勘記等,其內容有溢出於九大版本系統之外的異文,以及關於文字是非的判斷,擇要錄於各條校勘記之末,作為參考。
《十三經注疏匯校》出版的形式是:正文影印明北監刻《十三經注疏》初印本,並參考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之句讀,加以斷句,以便讀者。《匯校》列在每卷之後。每條校記均註明原本卷幾第幾頁第幾行,然後摘句,羅列各本異文。
匯校工作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杜澤遜主持,計劃2012年啟動,2018年完成。
《十三經注疏》點校通行本
根據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的體例,各經註疏均應選擇內容較全、錯誤較少的版本作為底本,其他版本作為校本,凡底本不誤而校本誤者,不出校勘記。凡底本誤而校本不誤者,則據校本改正底本,皆出校勘記說明。凡底本與校本不同,難定是非者,亦出校記說明。從而形成一部錯誤最少、附有簡明校勘記的通行本。這樣的通行本適合於一般研究者、一般讀者閱讀使用。但是,確定異文的是非直接關係對經典的理解,而對經典的理解從來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所謂通行本是極其嚴肅的學術成果,必須由經學造詣較深的專家承擔整理任務,並且應當聘請專家委員會做最後的審定工作,從而形成代表當代國家水平的最好的版本。《十三經注疏》點校通行本工作是《十三經注疏》整理計劃的最終成果,應當分別聘請有名望的專家承擔點校工作,點校的基礎是《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工作與匯校工作可以交叉進行。
點校工作計劃在2014年啟動,2019年完成。
(據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鏈接:關於《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注疏》是我國古籍中的基本典籍,是中國經學史上漢唐經學成就的代表,與“二十四史”構成傳統典籍的骨幹,歷來受到研究學習中國傳統學術者的最大重視。因此,《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的系統整理、刊行,歷來是國家高度重視的課題。尤其是明清兩代,朝廷主持校刊《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明代“二十一史”)已形成傳統。明代南京國子監有系統修版印行的《十三經注疏》,北京國子監有重新刊行的《十三經注疏》。清初仍用明代北監版修版刷印《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到乾隆前期則由朝廷組織優秀的學者系統校勘、刻印了著名的殿版《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乾隆後期又出現了《四庫全書》本《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薈要》本一般認為與《四庫全書》本為同一系統)、“二十四史”,也是精加校勘、自成系統的本子。嘉慶間,江西巡撫阮元在南昌刻印了《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乾隆殿本和嘉慶阮元本兩大系統的《十三經注疏》都附有校勘記,從而形成了經典整理出版的模式,即詳加校勘,然後刊印,附有校勘記。嘉慶以來近200年間,學術界使用的通行本《十三經注疏》仍是阮元本。隨著近年《四庫全書》影印行世,阮本之外,殿本和庫本也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
建國後,“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已經由國家組織優秀學者整理出了迄今最好的點校本,由中華書局出版,成為具有時代特點的通行本。“二十四史”至今還在進一步完善。這說明正經、正史的整理工作是一項複雜的、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遺憾的是,由於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的《十三經注疏》的版本沒有和“二十四史”同時產生。近年學術界和出版界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出版了若干點校本,但是這項工作仍有進一步努力完善的餘地。
儒家經書在流傳過程中,經歷了白文無注階段、經注合一階段、經註疏合一階段、經註疏音義合一階段。目前通行的《十三經注疏》總體上是經註疏音義合一的文本。學界認為,整理校勘“十三經”應當根據版本演變的階段分別進行,欲追尋經文之面目,應以較古之白文本為底本(現存唐石經本、宋版白文八經本雖為白文無注,實出於經注本而刪其註文,非單經原本也),匯校古本系統,包括出土文獻、古書引經等,並且參校《釋文》、經注本、註疏本。欲追尋經注本之面目,應以較古之經注本為底本,匯校古本系統(唐石經應歸入經注本系統),包括利用疏文以校經注(王鍔先生《禮記鄭注匯校》可仿效)。欲追尋《釋文》之面目,應以單行宋版《經典釋文》為底本,匯校舊刻舊鈔本,包括經注音義本、經註疏音義本內之音義部分(黃焯先生《經典釋文匯校》可仿效)。欲整理《十三經注疏》通行本,則應選擇單疏本、經註疏本、經註疏音義本進行校勘,而以相對完整之經註疏音義本為底本,否則經註疏音義之異文或無可附儷。蓋註疏本之整理與旨在恢復經書古本面貌之校勘實非一途,不可兼顧。白文原始文本已難求其全,故白文本原始面貌之探求大抵只能零星從事,難成系統成果。經注本之匯校、註疏本之匯校均有形成獨立系統的條件。
過去的校勘學家和經學家,把校勘的主要精力用於追尋經書及古注的原貌上,在出土文獻、敦煌殘卷、傳世古寫本、石經本、古刻本以及類書、古注引經等材料的校勘考證方面,作出了豐富的成果,總結出若干經書文本演變的規律,為釐清經書流傳史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對唐宋時期出現的“疏”,則校勘工作相對較少。已有的成果主要是:乾隆武英殿本考證、《四庫全書》本考證、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劉承幹刻若干單疏本校勘記等,其中阮元《校勘記》成就最大。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阮元通校的本子為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陽閩刻本、北監本、毛本四個版本,其他單疏本、八行本、南宋十行本,大量沒有直接校勘。例如《周易註疏》,阮元《校勘記》未見最早的宋刊單疏本《周易正義》十四卷,僅據錢遵王校本,而錢校本包括單疏本一種、單注本二種、註疏本一種,無法區別,阮校籠統地稱為“錢校本”,單疏本的面貌無法體現。阮元也沒有見到傳世較早的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周易註疏》十三卷,僅據盧文弨傳校明末錢求赤校影宋抄本,輾轉傳錄,難以保證校勘記的客觀性。同時,阮元沒有對校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本和《四庫全書》本,而這兩個乾隆本都是精加校勘並且附有考證(即校勘記)的版本。例如《四庫全書薈要》本《周易經傳註疏》,據其提要,是“以內府刊本繕錄,據宋槧本、明國子監本、毛晉汲古閣本及諸家所勘宋本恭校”的。而在今天,南宋刻單疏本有民國間傅增湘影印本,宋刻八行本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合單疏本、八行本、元刊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注疏》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注疏》本、明毛晉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清嘉慶阮元刻本等九種重要版本形成《周易註疏匯校》,就可以大大彌補阮元的《周易註疏校勘記》,從而真正將《周易註疏》宋代以來的主要版本的文字異同匯為一編,為進一步整理《周易註疏》更好的通行本打下堅實的基礎。其他各經註疏,阮元《校勘記》在網羅宋元舊刊、利用乾隆善本方面也普遍存在嚴重的不足。(本報記者 吳昂)